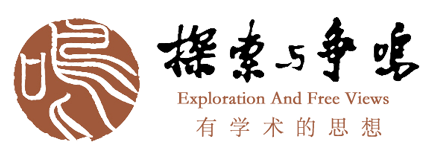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问题与对策
2016 年底,《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年度热词,该说法甫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后真相”不仅总结和凸显了2016年国际政治的现状,反映了国际大环境的时代特色,而且超越了政治领域,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数据时代,权力、技术的深度介入,真相变得面目可疑,甚至面目可憎,谎话、流言、绯闻以真相的幌子在网络上肆意流传,而真相却不知所踪。相对于过去人们对真相和真理的孜孜追求,后真相时代的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把立场、情感和利益置于真相和真理之前。这样的深层次危机,无论是对良性社会的建构、共识的形成,还是公信力的提升以及政权的稳定, 都是不利的,有必要认真审视和分析。更重要的是,后真相所表征的种种问题,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犬牙交错的中国,亦有所呈现。后真相问题不仅仅是认识论和信息传播的问题,其在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没有社会共识就没有经验事实的真相。后真相这个与后现代密切相关的概念,不仅揭示了中国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价值难题,而且反映了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诸多深层问题,亟需从多维视角来予以应对和解决,以世界眼光为中国问题把脉。近日,本刊编辑部与《上海思想界》编辑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召开了“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问题与对策”研讨会。本期刊发论坛上部分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期待学界进一步探讨。
——主持人 阮 凯 杜运泉
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
吴晓明
一
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激荡变化,人们开始不无忧虑地谈论起“民粹主义”的话题。虽说这个术语或许并不准确,但似乎总是意指某种政治制度,尤其是指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之失范所形成的乱象。不仅如此,最近在欧洲又出现了“后真相时代”来临的惊叹。所谓“后真相”,无论其具体的所指所用如何曲折隐晦,却总意味着真相、真理的消退隐遁,意味着坚实的客观性已然坍塌而不再具有约束力了。
虽说我们对这类现象尚未做过全面而专门的研究,但从哲学上来说,它们却决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东西。只有对现代性完全非批判的观点才会对此感到莫名惊诧,仿佛那是来自外太空的邪恶入侵了尽善尽美的现代世界。且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无论是所谓的“民粹主义”还是所谓的“后真相”,都是现代性发展到特定阶段上的产物,是无限制的主观性,即“坏的主观性”——它潜在地包含在作为主体性哲学的现代形而上学中——之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就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指证纳粹主义乃是启蒙的辩证后果和理性主义的极致一样。
“坏的主观性”是黑格尔的一个术语,用以表示主观性的无限制扩张,用以表示主观主义的极致,用以表示主观性通过“坏的无限性”来拒斥实体性的内容,并以此来取代或冒充客观性。在黑格尔看来,客观性植根于真正的普遍者;而具有实体性内容的普遍者既不是主观性的无限集合,也不是它的平均数。举个浅近的例子来说,可以有一千种甚或一万种主观意见,但这些主观意见的集合或平均数并不就是真理;即便我们将这样的主观意见置放到“坏的无限性”之持续不断的扩张之中,在那里产生出来的东西也决不是真理。因此,在理论上试图通过单纯主观性的集合来建立普遍者或客观性的意图,从一开始便陷入到幻觉之中——这是一种特别属于现代并因而在现代世界中有其根源的幻觉。
社会契约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证。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卢梭的贡献在于提出意志作为国家的原则,然而他所谈论的意志,不过是特定形式的单个人的意志(费希特亦持同样的观点);这样一来,许多单个人之结合成为国家就变成了一种契约;但契约并不是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为其基础的”[1]。换言之,社会契约论只是以一种主观性的集合来冒充普遍者罢了。关于这种理论的情形,马克思说得更加明白深透: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猎人和渔夫),乃是18 世纪关于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而卢梭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关系的“社会契约”,乃是以同样的虚构为前提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 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2]
主观性或主观自由的发展,首先在西方文明的轴心期奠基中见其端倪:苏格拉底正是由于将这一点道说出来,由于这种被道说出来的主观自由与希腊的伦理传统相冲突而被判处死刑的;而柏拉图则是由于见诸这种主观性的巨大威胁,“为谋对抗计”,亦即为维护国家的实体性本质而写下了他的《理想国》。主观自由的一个更为持续和深远的教化过程通过基督教的发展而得以缓慢地实现,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那解除了一切血缘的、半血缘的、伦理的、半伦理的种种关系方始成立的“原子式个人”,是通过长期的基督教教化而为其做好准备,并在现代世界中以特定的方式而被巩固地建立起来。“人的自由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开始开花,并在人类诚然是一小部分之间成为普遍原则以来,迄今已有1500年。但是所有权的自由在这里和那里被承认为原则,可以说还是昨天的事。”[3]
如果说,我们终于看到主观性或主观自由在现代世界中的繁花盛开(其最突出的标志便是作为主体性哲学的现代哲学),那么,一方面,这种主观性或主观自由只是在现代世界中才得到其最充分和最彻底的发展,并在特定的阶段上趋于极致——“民粹主义”和“后真相”等等不过是其极致上的诸表现罢了;另一方面,这种主观性或主观自由的确立乃是西方文明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并且尤其可以在观念形态上被简要地看作是1500年基督教教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现代世界把握为“基督教的世俗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政治民主制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为作为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的“人的主权”,在政治民主制中乃成为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4];政治民主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但是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中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5]。
二
主观性或主观自由在现代的确立与发展,不仅开辟出崭新的历史纪元,而且创造出无比丰硕的文明成果,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现代世界的一切伟大的奇迹、业绩和收获,都是与之本质相关的。贯穿于现代文明之终始的主观性原则,并非从一开始就纯全立足于“坏的主观性”之上。虽说古典哲学时代的某些理论构造似乎以“坏的主观性”为前提,但就哲学思想的总体而言,就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生活的总体而言,主观性或主观自由的发展尚未无限制地激进化,它依然使自身保持在与真理、现实、实体性和普遍者的张力和统一之中,依然或多或少地守护着哲学上的“客观性(Sachlichkeit)告诫”。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莱布尼茨乃是第一个试图调解传统形而上学与近代科学的思想家:他一方面以其全部天才将新的科学思想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又认为古代经院哲学关于实体形式的教义乃是不可或缺的。这种试图将科学和哲学、主观性和实体性作为一个统一体来把握的巨大努力一直持续到黑格尔。
就此而言,“19世纪天真的特性就在于,它把对知识的巨大热情和对未来文明的信仰建筑在社会确认的道德程序这个稳固基础之上……然而在今天,这种对社会现实恒定性的意识已经变得完全不重要了”[6]。正是在这样的稳固基础和恒定性意识隐退消逝的地方,社会生活以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观念等才在总体上从属于“坏的主观性”。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将“坏的主观性”看作是一个价值判断,它只是指主观性被置放到“坏的无限性”(即可以不断向外扩张并因而是永远达不到的无限性)之中,并且用这种抽象的和形式的主观性及其集合来代替和冒充真正的客观性。只是在现代世界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时,“坏的主观性”才成为笼罩和支配一切的现实力量,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处可以见到其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表现,而“民粹主义”或者“后真相”等,亦不过是“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的极致后果罢了。
标志“坏的主观性”在总体上开始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伽达默尔在《20 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把一战定义为20世纪的真正开端,因为正是伴随着一战,出现了一种真正划时代的意识。这种意识是表示:在以往,“……资产阶级时代把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同对有保证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满怀信心的期待统一起来,但这个时代已经终结”[7]。换言之,这种划时代的意识表示:那个使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获得信念支撑的整个观念体系,特别是其实体性的内容——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永久和平的理性设计、经济和科技之合乎理性的无限制发展 ,以 及在一切领域中的“ 公理战胜”——第一次全面地、不可挽回地陷于瓦解状态中了。与这种瓦解状态相适应,标志“坏的主观性”之全面扩张的哲学格言通过尼采之口被道说出来——“上帝死了”。这位先前曾默默无闻甚至被看成疯子的哲学畸人,在大战之后很快被当作先知而受到推崇,事实上乃是其哲学之意义被重新发现了。正如海德格尔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上帝死了”并不只是某个无神论者的意见,它在尼采那里意味着:“超感性世界”——在包括现代形而上学在内的2000多年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中作为真理、理念、本质出现的整个实体性领域——腐烂了、坍塌了,不再具有约束力了。尼采的思想是以虚无主义(Nihilismus)为标志的,而“‘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尼采把对虚无主义的解释综括在一个短句中‘:上帝死了!’”[8]
随着超感性世界的崩坍垮台,随着超感性世界中一切实体性本质的消遁隐匿,随着“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虽则不同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对此会有不同取向的回应,但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以及一般的知识领域,似乎只剩下单纯的主观性在活动和起作用了。正是这种时代境况推动了主观性的无限制发展,从而使“坏的主观性”在历史的现实中,也在观念的形态中占据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真相”或“民粹主义”等现象的研判和讨论,就其哲学上的深入而言,不能不使之在根源上归结于“坏的主观性”,并且不能不首先将其作为“欧洲虚无主义之降临”的一部分来把握,尽管此种现象之波澜所及和萌动发越决不仅限于欧洲或西方。
三
关于“后真相”的议题,看来是与公共舆论的境况所发生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而这种转折又特别是与媒体手段的变革(即“新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等)相表里的。在这样的转折过程中,公共舆论的性质和取向究竟在发生怎样的转变,并且在怎样的程度上使我们处于所谓“后真相”的境域中?如果我们就此来回顾一下黑格尔关于公共舆论的讨论,将会是很有裨益的。在黑格尔看来,现代世界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它以实体性的理念为根据,而且在于人的主观自由这一原则获得了重要性和意义,因此,公共舆论尤其在现代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然而,公共舆论乃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公共舆论一方面包含着永恒的实体性的正义原则等,并且正是这种实体性的东西构成公共舆论之内在的东西;但“在这个内在的真理进入意识并表现为一般命题而达到观念的同时……一切偶然性的意见,它的无知和曲解,以及错误的认识和判断也都出现了”[9]。因此,公共舆论的实存乃是经常存在的自相矛盾;在其中,实体性的真理和无穷的主观错误是直接混杂在一起的。我们由此很容易理解到的一点是:当实体性的东西在公共舆论中瓦解陵替之际,这个领域也就为“坏的主观性”所占据,以至于到最后完全成为各种主观意见的集合,成为它们彼此之间冲突驰骋的战场。用“后真相”一词来标志此种状况是合适的,因为所谓真理、真相总是同普遍者、同实体性的东西内在关联的。毫无疑问,黑格尔对“坏的主观性”的批判乃是完全正确的,其哲学的偏谬则是在另一方面。关于这一点,洛维特说得对:马克思之所以捍卫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理解普遍者的决定性意义;而马克思之所以反对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把普遍者或实体性的东西神秘化了[10]。因此,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观察到所谓“后真相”时代的种种表现,那并不是因为神秘的绝对理性在自我活动的行程中通过“坏的主观性”来达到其实体性的自我否定,而是“市民社会”的现实(“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哲学上表现为主观性的无限制发展,并在其特定阶段上抵达或可称之为“后真相”的极致。
所谓“民粹主义”的问题境况大体也是如此。在关于政治制度的哲学讨论中,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一般来说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原则的,但这应当被理解为“实体性的理念获得了无限的形式”,应当被理解为作为实体的善“在客观的东西中充满着主观性”[11]。在黑格尔之前,无论是在现代的政治哲学还是在现代的政治实践中,实体性与主观自由的调和在历史的客观态势上始终是存在的;即使是那些似乎完全建立在“坏的主观性”之上的理论构造,也从来不缺乏使之与实体性相勾连的各种资源。我们知道,虽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免于“坏的主观性” 之幻觉的批评,但他还是区分了所谓“众意”(诸主观性的集合或平均数)和“公意”(具有实体性内容的普遍性)。毫无疑问,黑格尔非常正确地意识到:“坏的主观性”乃是自相矛盾的东西,并因而是使自身趋于瓦解的东西;但黑格尔力图使之与实体性相调和的努力最终是失败了——一方面由于其哲学的思辨性质,另一方面由于现实历史的实际进程。
正是马克思彻底纠正了黑格尔:“坏的主观性”的观点即“原子论”的观点并不是什么“令人诧异的东西”,也不是可以用思辨理性的观点就可以改变的东西;如果说某种观点是原子论的(即立足于“坏的主观性”之上的),那只是因为市民社会本身是原子论的,因为市民社会本身是以原子式的个人为前提的。[12]因此,事情的本质乃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发展及其客观的历史趋势,而这种趋势不能不表现为“坏的主观性”达于极致并使自身进入到终结阶段。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现代选举和选举改革(作为趋势) 时指出:选举是市民社会对于政治国家的直接的和实际存在的关系。“通过不受限制的选举和被选举,市民社会才第一次上升到自身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真正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但是,这种抽象之完成同时也就是抽象之扬弃……因此,选举改革就是在抽象的政治国家的范围内要求这个国家解体,但同时也要求市民社会解体。”[13]没有什么比这一论断更简要地揭示出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历史趋势及其历史限度了。那被称之为“民粹主义”的种种现象,如果不是“坏的主观性”即“原子论”之抽象的完成,又会是什么呢?
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所谓“后真相”和“民粹主义”等现象,显然还需要做许多专门的研究,才能对之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判断。然而从哲学批判的视野来看,它们乃是现代性发展在特定阶段——终结阶段上的产物,其本质方面应当被把握为“坏的主观性” 之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3][9]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55、70、33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4][5][12][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79、196、99、150.
[6][7] 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10、108.
[9]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766-767.
[10][11] 洛维特. 从黑格尔到尼采.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127、165.
“后真相”中的“真相”
孙江
当前,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思 潮弥漫全球。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胜出,不仅让媒体事前的预测大跌眼镜,也使反智主义一跃而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2016 年11 月16 日,《牛津英语词典》将post-truth(“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认为“后真相”反映了2016 年是“非常紧迫”的政治性的一年。同年12 月9 日,德语协会也将“后真相(postfaktisch)”选定为年度词汇,指出与事实相比,“俨如感同身受”。套用黑格尔的句式,“后真相”是情感在先,事实在后。其实,当下公共舆论中的“后真相”不过是彰显了其内涵中的非理智倾向而已。
在西语中,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 ?ffentlich- Meinung/opinion publique)作为整词出现于17 世纪, 及至18 世纪后半叶逐渐成为一个主导性的政治-社会概念。在西欧世俗化过程中,由于人从神的永恒的普遍秩序被抛入具有偶然性的时间世界,“公共”是在流动的、碎片化的不安定的社会空间中逐渐生成的,启蒙思想家将自古希腊以来的公(kοιν?ν/publicus)先于私(?διον/privates)“转向”,认为国家乃是为了保护和促进个人利益而创造出社会的。对于舆论,除了与古典真理和意见含义在唯名论上加以区别外,启蒙思想家认识到舆论附带行动,蕴含政治力量,是打破政治隐秘性的利器。鉴于此,主权者基于维持秩序的要求,常常否认公共舆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基于文化教育、技术手段和权力分配等因素,人们对公共舆论的参与和感受也不尽一致,公共舆论无法吸纳所有人的诉求,其诉诸理性或情感的性格为反智主义预留了滋生的空间。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认为“理智没有人气(un- popularity of Intellect)”[1],从美国建国到1950 年代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文化中流淌着绵绵不断的反智主义的潮流。霍夫斯塔特用以分析美国这一特定政治-社会环境的反智主义概念工具,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可以解释其他地区和国家存在的类似现象。
不同的是,当下的反智主义滋长于新的知识/权力氛围,是在全球化/匀质性和地域化/特殊性的张力关系中不断发酵的。传媒技术的革命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弱化了原有公共舆论的媒介功能,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新媒体获取所需信息。只要有网络,一台电脑或智能手机,即可将海量的信息尽纳囊中,足不出户而知晓天下。英国社会学家霍斯金斯(An- drew Hoskins)认为,这是“连接性的转向(connective turn )”所带来的“活着的档案(the living archive)”的吊诡现象。一方面,它穿越看似健忘、抹去了过去感的日常数字通讯,通向即时性;与此同时,比起以往的媒介,它又使过去显得近在眼前和触手可及。[2]如此一来,“客观事实”不再由公共舆论来主导,而取决于分散化的小群和个体的好恶与取舍,恰似英语和德语中的诙谐调侃:letter(文字)即 litter(垃圾),Druck(印刷物)如Dreck(排泄物),公共舆论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存在。
不止于公共舆论,公共历史也遭遇同样不确定性的难题。本来,情感先于事实是历史叙述的伴生物,没有哪种叙事不曾掺入个人的情感和信仰。19 世纪实证主义历史学矫枉过正,追求“赛先生”,这一刻板的叙述样式为20 世纪史学家所扬弃,年鉴学派拓展历史学的领域,关注政治以外的社会、经济、心性等,而“公共史学”则大开门户,强调历史学与当下的互动。“历史”原本属于职业群体——历史学者耕耘的田野,历史叙述进入公共领域之后遭遇到其曾极力规避的问题:情感先于事实。年鉴派学者费罗(Marc Ferro)将公共历史叙述中的这一现象称为“沉默”,体现在正统性原则和集体记忆方面。[3]他认为,在涉及正统性起源问题上,不管是教会和王朝,还是政党,历史叙述的机构都缺乏“透明性”。确实,如果说公共历史是一种知识性的存在的话,无论从王权的谱系到近代国家的谱系,都多少纠缠着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随着世代的推移,当言说变成自明的知识并内化为共同体的集体情感和信仰后,一种如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记忆的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便形成了,它影响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在时间之流中依“分散法则(a law of fragmentation)”和“集中法则(a law of concentration)”而变迁。[4]
费罗的沉默类型学分析还涉及两个相反的样态:加害者的沉默和受害者的沉默。所谓加害者的沉默是一种内化的、心照不宣的沉默。20 世纪末公共历史领域最重要的争论,是围绕历史修正主义言说展开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奥斯威辛犹太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受害者/历史的“不在场”,给历史修正主义者以否定历史“实在性”的借口,充当了“记忆的暗杀者(assassin of memory)”的角色。[5]朴素的实证主义者希冀以铁证如山般的史事进行回击,其实,经历“精神创伤(trauma)”的受害者除了“受害”本身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的案例,在心理学和历史学上不乏其例。比起虚实杂陈的回忆来,回忆不起来本身就是受害事实的最有力的证据。这涉及费罗所说的受害者的沉默问题。记忆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的兴起,直面的是当事者即将成为“过去”的现实,抢救当事人的“历史”使记忆研究在公共史学中成为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回忆(?ν?μνησι?/anamnēsis)是一种对于外在刺激而进行感觉和推理的过程,古希腊语中意为自下而上的精神活动。对于难言之隐,当事人常常选择沉默,这最终导致集体记忆的丧失。
以书写为特征的历史叙述始于口传时代,口述史的兴起犹如历史叙述“返祖”。主编《记忆之场》的诺拉(Pierre Nora),质疑口述史到底是当事人的历史还是设问者的历史。[6]我以为,问题的核心在于个人口述多大程度上是属于个人真正经验的事实,按照哲学家利科(Paul Ric?ur)的说法,记忆要成为公共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经受检验。[7]个人的证言是从诉之语言记忆开始的,被讲诉的记忆从一个体制(集体)向另一个体制流动,进而进入公共领域。证者言之凿凿,闻者未必尽信,甚至怀疑。这样,证言就需要接受验证,不能经受诘问的证言就不能称为事实。各种证言进入档案馆,和其他有些完全不是证言的证据一起被收藏起来,进入了史料范畴。史料超越记忆痕迹,是记忆所无法匹敌的真正制度化的东西。根据史料痕迹和记录文书,认识论建构起其相应的阐释范式。史料交由专家来判断、解释,其真实性是由史料的盖然性所决定的,有多少比例、是否首尾一贯、有多大的有效性等。历史的真实仰仗史料和记录,胜过记忆的真实度。利科认为,历史判断嵌入现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构成历史母体的集体记忆只有再次作为历史的累积和媒介才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正如当年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批评哈布瓦赫时所说,即便记忆是集体的,也无法将记忆主体归于集体这一实体之中,而且一旦将“集体”这一形容词视为有如个体一样可以“回忆”,则会陷入将集体视为一个自明的实体的危险。[8]因此,口述史、记忆研究等当下公共史学还需要有一段内省和批判的路要走。
于是,围绕“后真相”的博弈转移到认识论的领域。在“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之后,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揭示了“超历史(metahistory)”——meta/μετ? 不是“之后”,是“超越”之意——的文学性格。[9]这如一记炸弹,震撼了历史学的脆弱神经。论者可以不赞成怀特的观点,但不能不正视他所提出的问题:历史学的文学源泉、批判性意识形态以及历史如何成为一门学科等问题。[10]
事实上,由文字所承载和传递的过去的信息,通过回忆而建构的过去的经验在记忆中是解释学的经验,如何寻觅不在场的实在呢?1970年代以降,“语言学的转向”动摇了科学地说明过去的信念,但历史学者并没有放弃对历史合理性的探求和对历史现实的重构。[11]新文化史大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 质疑怀特对“历史的想象力”与历史证明之间的相互作用、被视为文学的历史作品与历史研究的历史著述之间的相互作用缺乏必要的说明。历史学有自身的自律性,从“证据”到“事实”尚有弥合的可能性。金兹伯格认为,史料存在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假的(fake);一种本身是真的(authentic),但不可信(unreliable),因为提供者可能说谎或有误;一种是真实的和可靠的(authentic and reliable)。在此,史家可以排除前二者,针对第三者进行历史性的研究。[12]文字通过视觉将语言符号化,而痕迹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现为痕迹的史料两相对立。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回忆空间》一书中,专门讨论“文字(schrift)”与“痕迹(spur)”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痕迹里既含有逝去的文化的非语言表现——废墟和遗物、片断与碎片,也有口传传统的残滓”[13]。把“痕迹”作为非文字之物,强调痕迹的意义大于文字。这类对历史事实的探索不无效果。2009 年10 月24 日,年届80 高龄的怀特在日本东洋大学做《实用的过去》的长篇演讲,承认在围绕“事实”与“虚构”关系问题上“,我曾犯过错误,现在清楚了。也许这样论述与话语(历史学)的关系较为妥当,即在试图忠于指示对象的同时,产生了文字记述以外的意义,就其结果,虽不能说是虚构,但无论怎么看承继了文学表象习惯的话语”[14]。至此,纠缠多年的悬案似乎告一段落了,但是怀特又将球踢给了历史学者。何以历史学看起来像文学呢?对此,历史学者应该予以认真回答。
同样,在批判“后真相”的反智主义倾向时,霍夫斯塔特笔下的知识人是否也该反求诸己,省思自身的欺瞒和傲慢。反对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致力于揭示近代知识的断裂和非连续性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晚年回到古希腊,大谈真理,陈述“ 直言(παρρησ?α/parrhēsia)”在古希腊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所谓直言,简言之,就是不畏危险勇敢地讲述真理。面对反智主义时代的来临,重温“直言”,如何把握和讲述真理呢?这个严肃的问题等待每个思考“后真相”者的回答。
参考文献:
[1] Richard Hofstadter.Anti- intellectualism in Ameri- can Life.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3:24-25.
[2] Andrew Hoskins.Media,Memory,Metaphor:Remembering and the Connective Turn.Parallax,vol.17. no.4,Routledge,2011:19-31.
[3] Marc Ferro.L′Histoire Sous Surveillance,Calmann- Lévy,1985:52-59.
[4] Astrid Erll·Ansgar Nünning.Cultural Memory Stud- ies: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Walter de Gruyter·Berlin·New York,2008:148.
[5] Pierre Vidal- Naquet.Assassins of Memory:Essays on the Denial of the Holocau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6] Pierre Nora.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Les Lieux de Mémorire. Ⅰ.La République,Paris:Gallimard,1984.
[7] Paul Ric?ur.Zwischen Ged?chtnis und Geschichte.Transit ,22(Winter2001/2002).
[8] Marc Bloch.Mémorie Collective.Tradition Et Cou- tume.Revue de synthésehistorique,1925:118-20.
[9] 海登·怀特,陈新译.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10] H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99.
[11] 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 tion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and Present,No.135,1979.
[12] Carlo Ginzburg.Checking the Evidence:The Judge and Historian.Critical Inquiry,Vol.18,No.1,Autumn, 1991.
[13] Aleida Assmann.Erinnerungsr?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chtnisses.C.H.Beck, 1999:209.
[14] ヘイドン·ホワイト.実用的な過去.思想,2010(8).
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
蓝江
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无论是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是主要的高校中的调查机构,都一时间陷入了窘境。他们感到最为窘迫的,并非是作为右翼保守主义的势力在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下重新崛起,而是他们在选举前做出的种种预测和调查几乎全部出错了。最终的结果让所有预测机构和学院派都感到大跌眼镜,原因并不是他们认为自己在数据分析上出现了差错,没有严格按照政治科学分析和数据分析的程序来循规蹈矩地得出结论,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十分严格地执行了这个学科性的规定,并最大程度上依循最客观的数据上的结论,而最终的结果却谬之千里,这才是令他们感到最疑惑不解的地方。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原先只在哲学圈子里流行的词汇“后真相(post-truth)”,一跃成为自2016 年 11 月以来的各大媒体上最流行的词汇之一,而随后《牛津词典》公布的2016 年的年度英语词汇,正是“后真相”。那么,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到一个后真相时代?后真相对于我们来说,尤其对于政治决断来说意味着什么?
首先,什么是真相?从本体论上来说,真相并不能直接向我们敞开。也就是说,从康德之后的哲学,相信我们总是在一定的关系中来理解我们与真相的关系,而并非真相直接出现。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感知是极为碎片化的,零散的经验材料不足以传递出事物和客观事实的全部真相,这样,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充。而这个补充恰恰是依赖于某种结构向我们的再现(representation),如先天观念、语言、格式塔、内意识,甚至近来在哲学中谈到的影像和神经元结构, 等等。简言之,我们所谓的真相,永远是经过一定的结构性或程序性处理过的被再现的“真相”,真实的真相永远会和我们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当然,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会因此囿于这个认识论上的藩篱,一定会使用各种方法去趋近于真相。在趋近于真相的过程中,也就是一旦我们走出自我意识的圈子,面对所谓的真实世界的时候,一定需要某种工具,而这种工具是作为我们前行的基础和支撑。在现代哲学诞生之前,在中世纪信仰为主的阶段上,支撑落实在上帝的全知全能基础上,因为所有真理或真相的保障,恰恰在于那个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的主那里。现代性启蒙的祛魅掩盖甚至消除了这个最终保障,最终将我们建立真相的保障落实在两个基础之上。
其一,理性推理的出现,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支点推理出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无论是阿基米德的支点,还是笛卡尔悬搁了一切判断,最终从“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开始演绎出整个第一哲学体系,实际上都依赖于一个绝对不可否定的命题,即一个最初的原点来演绎出世界的知识体系。但这种演绎的结论早就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中遭到了质疑,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无法在我们的经验之外寻找到一个确凿无疑的支点,作为我们演绎逻辑的第一步骤。休谟更是将演绎逻辑借以衔接逻辑推理和现实世界的因果关系,推上了审判台。在新实用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之后,演绎的形式逻辑只能保障在逻辑演绎自身的自洽性,即从一个假设的命题出发,推理出一个结论,并保障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具有真理性。相反,一旦面对真实的世界,逻辑学的主张会保持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其根本也正是在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绝对被认为是真理的逻辑推理的起点,这样也势必意味着从演绎推理的角度获得真相的途径,已经遭到了巨大挑战。
其二,现代科学的兴起,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兴起,让基于实验数据而推理的方式获得了推崇。相对于演绎推理,归纳性的数据分析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推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也能够提供关于真实世界的真相。因此,实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得出的相关的结果,可以作为我们接近真相的基础。简言之,科学数据和计算提供的是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而这个客观性基础,正是使现代科学成为科学的东西。在整个科学史发展过程中,以数据和事实归纳形成的客观性,并不是一开始都十分顺利,如意大利天文学家皮亚齐在1801 年观测谷神星收集的数据,不足以形成对谷神星运行规定的判断,原因并不是数据过少,而是数据过多,以至于任何一条现实的轨迹都无法满足所有观测数据的值,因为皮亚齐面对的是过多数据构成的超定方程组。后来是数学家高斯通过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主观优化,从而既平衡了各个数据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准确地预测出谷神星的位置。这样,基于观测数据和事实为基础的客观性,成为我们在今天理解真相的最后保障。在任何观念和知识不能提供真相的保障时,数据的收集、分析、计算、归纳得出的结论成为我们探索真相的最为重要的根基。
在这个基础上,数据、信息、数值成为当下客观性真相的唯一保障。这种保障不仅仅出现在科学领域,也出现在类-科学(quasi-science)领域,比如对社会现实、政治状态、新闻传播的影响、心理结构等,都会使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同时现代人也意识到,我们对真相的了解也不能完全依赖于数值分析和计算,因此,各个学科都会采用质性方法来平衡数值分析和计算、数据统计产生的结果。比如说社会学中的民族志或田野研究,就是对数据收集与分析的一种平衡,但是这些质性研究方法,不能单独作为获取真相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无论是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 还是政治学,质性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数据和数值的客观性研究的补充出现的。它一方面补充了数值分析所不能说明的情况,也平衡了数据和数值分析中过于僵化的情形,但所有这些都必须以客观数据为基础来说明真相。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之前,人们会如此看重各大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分析。新闻机构以及专门从事调查分析的学术机构, 所从事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都是严格按照教科书式的方式来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获得的数据没有弄虚作假,全部是真实有效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并非虚假的结论(作为客观性的结论)与最后的历史性结果截然相反,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实上,正如有人指出,民调机构和媒体预测在美国大选历史上并不是没有错过,例如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时,著名的民意测验机构盖洛普预测的是杜威获胜; 而同样在肯尼迪和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时,在二人电视辩论之前,媒体预测的也是尼克松获胜。但是,之前的预测出错的时候,人们更愿意解释是某种调查的设计上有缺陷,以至于某些因素没有被纳入到调查的考察之内(例如第一次电视辩论的尼克松明显在形象上败给了肯尼迪,而媒体的参数设定的还是从政经验、学历、外交能力等方面)。此后,媒体认为,不能过多地信任某一家(如盖洛普)机构的调查预测,应该让调查预测多元化,用多个不同机构和民意测验来平衡某一家权威机构的分析结果。在此后的过程中,由于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多元化,让后来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基本上是符合大多数民意测验机构和媒体预测的结论的。在这个意义上,多元化的数据分析继续充当了真理或真相的客观性基础。
然而,这次的民调和预测分析却与以往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是,不仅仅是绝大多数的预测错了,而是几乎没有民调和预测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就不是某个机构在调查设计和统计上的缺陷,而是整个作为客观性基础的数据收集与分析遭到最彻底的质疑。因为,在几乎所有预测都出错的情况下,人们怀疑的目标不再是某个机构调查和分析的合理性,而是数据作为真理客观性基础的合法性。长期以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数据成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事实的支撑。但是,在当下的背景下, 数据及其分析已经不能为我们提供触及真相的路径。这样,作为客观性基础的数据分析遭到了挑战,这种挑战的结果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数据分析和归纳来获得真相。
但是这个结论很容易被蒙昧主义所利用,也就是说,由于数据在调查分析上的漏洞,以及在预测上的失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直接宣布,作为实在论根据的数据客观性不再有效,数据分析的结果与主观臆断实质上没有什么两样,而数据的客观性,实际上不过是伪装成客观性的主观性,对于这些人来说,数据的选取和甄别已经出现了主观判断,而这种主观判断的倾向性会导致预测的偏向。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人们更愿意用主观立场,而不是客观事实来判断一个数据预测的真实性,在主观价值介入之后,人们更愿意相信某些数据,而不相信另外一些数据。例如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后,截取了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证明自己的“限穆令”是他执政以来最受欢迎的命令,并借此来挑战联邦法院的裁决。而在政治立场的另一方,他们也有相关的数据证明总统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样来看,由于调查统计和预测的多元化,数据的客观性变成了粉饰各派立场的一个装饰物,它们不再是通往真理大门的唯一途径,而是用来巩固不同政治立场的一种武器,借此来攻击和挞伐对方的论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真相变得不再重要,媒体和预测机构以及行政部门,他们关心的不再是事实上的真相如何,而是以主观立场介入的后真相。后真相被形容词化,它所修辞的名词正是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立场、观点。
我们看到,马克斯·韦伯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和事实原则已经在今天被虚无化了,那种可以在各种价值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便无偏倚地得出客观性的结论,已经明显不符合后真相时代的话语。在韦伯所开创的时代中,客观性的事实原则是获得真理的最后屏障,也是社会科学得以建基的唯一基础。所有的主观立场,只有经过客观性(尤其是以数据为中心的客观性)的准绳检验之后,才能纳入考量,否则就是前现代的带有魅惑性的价值判断。在韦伯看来,尤其是在他的《以学术为业》的讲座中,价值中立的事实原则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伦理,无论持何种立场,都必须在客观性的标准面前进行检验,这是一种客观性优先于立场的原则。
然而,今天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数据、统计、数值分析得出的客观性结论遭到质疑,客观性的价值只剩下用来装点不同的政治立场,每种立场总能截取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分析,从而将与自己相悖的数据弃之不用。这样,真相优先于立场的原则被颠倒为立场优先于真相,重要的不再是客观性的数据所再现出来的事实。因为在今天的背景下(尤其经过利奥塔、鲍德里亚、维利里奥等人之后),能被数据和事实所证明的真相被边缘化,他们发展出来一套拟像体系,提出了比真实更真实的原则,从而直接消除了唯一真相的合法性,让拟像的真相取代了原本的真相。这样,在哲学上,经过鲍德里亚等人洗礼,真相直接过渡到后真相,真相变成了复数的真相,每一个真相只是面对一种特定拟像下的数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那个最终的真相,因为最终的真相下面,永远有一个需要发现的真相在等着我们。
尽管我们大可不必随着鲍德里亚的姿态走向真实的虚无化,但是,我们的确面对一种状况,原来支撑真相的两大基础都崩溃了,即作为普世性的理性原则(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演绎推理逻辑,甚至连哈贝马斯所提倡的协商和交往理性也一并被质疑),以及作为经验性数据收集、统计、分析的客观性结论。这两个基础恰恰是现代社会和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石,一旦崩塌,人们唯一可以诉诸的就是主观性原则。这或许可以解释在今天为什么已经被现代性所祛魅的宗教,重新在21 世纪的世界里大行其道。一旦客观性原则和理性原则不再成为接近真相的途径,人们就会摒弃向外部寻找的事实性依靠,从而转向内部,寻求内心中的慰藉。也就是说,在今天,更容易影响人的行为决策的不再是客观事实,而是内心的信仰和情感依靠, 人们不是在理性分析和判断数据基础上做出决定,而是转向内心中的立场和情感。我们很难在当下去说服一个穆斯林返回到世俗化的道路上,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指望理性的说教可以改变一个特朗普的信徒的投票选择(尽管这个信徒可能在民调采访时自然选择政治正确的说法,但投票时会转向另一方)。这是一个立场先于真相的时代,也就是被媒体高呼的“后真相”时代。
是否在这个“后真相”时代里,真相和客观性真的终结了吗?我们再也不能相信科学预测的结论了吗?当代的哲学家们并不这么认为。法国哲学家昆汀·梅亚苏将这种蜷缩在立场之中,用立场来判定真相的方式称为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而真正需要打破的恰恰是相关主义建立的死循环,因为在相关主义的立场之外,还存在着永远不能被观念化的物质性的原化石(arche-fossil)。巴迪欧在他2006 年的《世界的逻辑》中,也强调这个世界除了语言和身体之外,还存在着真理。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真相,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鲍德里亚等人的语言魔术,只能是智术师一般的诡辩,这种诡辩无法从实在层面彻底消灭真相的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以及梅亚苏等人,坚持将这种原则称为唯物主义或者实在论的原则,而这种原则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消解相关主义的“后真相”判断,让那个真相的硬核从现实中浮现出来。
这样来说,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恰恰不是意味着真相的破产,而是意味着原来没有被我们的认识所把握的真相的硬核的浮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化约为民粹主义立场或保守主义立场的复兴,而是要意识到这些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合理性。对于一种黑天鹅现象的简单命名(如民粹主义) 很容易,但是,这种命名恰恰是背弃真相的,是这种民粹主义命名直接将真相的内核转化为所谓的“后真相”,并借此来否定真相的价值。其中的最大优势在于,在掩饰了客观性真相之后,能直接满足他们用主观性的立场判断来引导人们的行为。所以,在“后真 相”时代,我们恰恰需要重新高举真相的大旗,因为不是没有真相,而是以往我们接近真相的方式都出现了漏洞,需要重新在更宏大的背景下,重建一个可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而不是让真相留下的空位直接转移到主观性之上。否则,我们的社会必然会被彼此充满敌意的主观立场性的判断主导,我们今天看到的白人保守主义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对垒,实际上就是一种彻底摒弃了真相客观性之后的“后真相”的立场对垒。所以,作为一种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仍然需要将真相,尤其是物质客观性真相作为探索的目的,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这个真相是什么。这种有漏洞的真相或者所谓的思辨性的唯物主义,才是我们可以摆脱纯粹主观主义的站队,摆脱以立场优先来做判断的“后真相”时代的可能途径。
“后真相”本质上是后共识
汪行福
“后真相”一词的出现在“ 后”时代是不难想象的,正如“ 后历史”“ 后现代”“后民主”“后人类”等词一样,只需要在“真相”或“真理”前面加以“后(post)”就构成了。如果“后真相”概念对理解当下具有症候学意义,它所表征的就不应该仅仅是某个事件及其后果,而必须指认出今天社会的历史性存在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笔者认为,后真相的本质是后共识。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观念传达与接受之间就会短路,其结果是,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或者拒绝真相,或者相信“另类事实”。这正是特朗普竞选的舆论攻防战中忠实选民采取的态度。
后真相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即认识论或形而上学层面、社会学或大众传媒生态层面以及政治学或社会共识层面。在认识论或形而上学层面,“后真相”并非是一个新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代和中国先秦就出现了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在它们那里,独立于主观情感和信念的真相或事实是不存在的。西方最早的怀疑论者高尔吉亚提出了三个著名的怀疑论命题:1. 无物存在;2. 如果有物存在,也无法认识它;3. 即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中国古代诡辩论也曾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学说。总体上说,中外古代怀疑论本质上具有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倾向,它或者认为任何判断都是因人而异的,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说“个人是万物的尺度”,或者认为对事实的真正判断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人的许多烦恼是过于较真,如果我们把一切判断悬置起来,就可以获得内心的宁静。显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后真相问题所关注的重点。但是,后真相概念的认识论意涵对我们的讨论还是有意义的。在认识论上,后真相无非是这样一种态度:或者认识真相是不可能的,或者认为真相是不重要的。其实,在认识论上真相问题是无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各执一词,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统一的定义。大致来说,在我们这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倾向于对真相做共识论的理解。所谓真相不过是相关的知识共同体对特定事物的共识, 在这里,客观性就是普遍性的主观性。显然,这一对真理的理解是非自足的,它依赖两方面的条件。一是研究者有认识真理的意愿,二是知识共同体对何谓共识有统一的标准。因此,真理依赖于对认知者的认识意愿和真理程序有普遍的共识。虽然哲学家关于何谓真理会一直讨论下去,但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今天对后真相现象的热议更多地指向的它的社会学层面和政治层面。
在社会学层面,真相问题是知识的生产和筛选问题。吉登斯注意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后传统社会,由于社会的流动性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人们的生活已经“脱域”,他们不再依赖本地性的习俗和个体的经验,相反,他们更多地依赖于专家知识。然而,专家在许多问题上看法往往是有分歧的,他们常常对同样的现象做不同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处在“解释冲突”的时代。另一影响我们获得真相的因素是真相的
“过剩”和“冗余”。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出现,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能是信息的公共提供者。一部智能手机可以摄影,发布信息,对信息进行评论。电脑可以对信息进行复制、拼贴,在这里,信息处在杂草丛生状态,信息不仅脱离其源头自行运动,而且超出提供者的控制自行繁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处在鲍德里亚所说的虚拟和超现实(hyperreality)时代。此处的“超现实”并非指比现实更高现实,而是说虚拟的现实被当作比现实更现实、更重要。按照经济学原理,从过剩和冗余信息中筛选出真实信息是有成本的,起码有时间成本。当这种成本过大时, 信息的接受者往往依靠个人的情感或习惯去选择。所谓后真相在社会学上可以视为新部落主义。我们无法作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和中立的判断者,我们只能依赖他人的影响,依靠自己群体内部的“共识”来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培根在现代之初说“知识即力量”,今天变成了“流量即金钱”“粉丝即权力”等,信息发布者有动机提供越来越多信息,不论真假如何。总而言之,如果权威知识本身已经陷入了解释学冲突,民间信息又出现泛滥和过剩的话,如何获得真相就成为社会的难题。
社会学条件对解释类似于“后真相”之类的社会现象是重要的,但“后真相”现象产生的更根本原因,还是真相的生产和传播所依赖的社会共识的瓦解。虽然此次英国脱欧或特朗普“逆袭”成功催生了“后真相”概念, 但要理解这一现象还需把它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上来考察。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社会的撕裂,使民意对真相的态度发生了扭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经济学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战后共识,即自由制度的存续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民主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支撑。前者驯服国家,后者驯服市场。一个合理的社会需要把自由、平等和民主结合起来。然而,这一对“法治国 家—民主制度—福利社会”结合体的共识被新自由主义社会瓦解了。新自由主义是市场主义,它试图通过经济全球化把所有国家结合到自由交换的全球网络之中。新自由主义对其合法性有自己的理解,在它看来, 资源、资本、人才和服务的全球自由流动可以提高相关要素的效率。市场经济是不平等的,但它所创造的效益可以通过“滴漏”效应惠顾所有的人。然而,西方正在品尝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哈贝马斯指出“:在那些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至少取得历史性社会政治成就的国家,失望的情绪正在逐步蔓延。世纪末,被社会福利国家制度驯服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新自由主义重新抬头。”[1]
近年来,西方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明显增加。拉克雷特的《债务人的形成》认为,西方国家已经沦为债务国家。“债务是对整个社会的‘猎取’‘吞噬’和‘榨取’的机器,是宏观经济调节和管理的工具,是收入再分配的机制,也是个人和集体主体的生产和‘管制’机器。”[2]债务机器把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人”变成金融资本主义的“债务人”,不仅通过生产榨取剩余价值,而且通过消费获得利润,因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施特雷克在《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中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虽然战后大众民主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暂时压制了这一矛盾,但当新自由主义把资本主义经济从民主国家的干预中解放出来时,整个社会就陷入了贪欲和恐惧之中。他说:“我们今天确实处在民主制度的晚期阶段,如我们所知,民主制度正在走向一条被阉割为再分配的大众民主,或者是被缩减为法治国家和公众娱乐的组合形成的道路上。”[3]但是,通过债务购买时间延缓危机是不可能永远奏效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资本主义是否进入到晚期阶段,但可以肯定,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婚姻”已经解体了。如果把施特雷克的表述稍微转化一下,我们就可以理解民主危机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关系。所谓民主就是把由合理的体制所提供的真相转变为有约束力的民主的公共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须会导致民主政治的危机。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可以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看法。当今资本主义是“世袭资本主义”或“遗产资本主义”,其根本特征是社会的再封建化。底层人面临着无法超越的天花板,富人把自己封闭在有门卫的社区里,社会分裂为对立的两极。
简单地说,西方面临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当经济发展失去了必要的互惠和共享性,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系就断裂了,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社会基本价值和社会共识的瓦解。可以说,即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不以美国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之类的戏剧性形式出现,它也已经瓦解了社会共识和“真相政治”的基础,最近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中出现的后真相现象,正是这一结构性危机的爆发。为什么社会共识的失落会改变人们对待真相的态度?我们在此想借鉴福柯的理论。福柯在去世的前一年曾做过有关直言或说真话(parrhesia)的讲座, 并把它视为西方批判传统的根源。Parrhesia在英语中一般译为“free speech”,但在希腊人那里,该词有着复杂的含义。首先,直言是坦率地说,直言不讳。其次,直言必须是说出真相,这种真相不是道听途说的,而是“他知道它是真的;而且他知道它是真的,因为它确实是真的”[4]。第三,直言与危险如影相随。一个哲人批评僭主是危险的,这个哲人就说了真话,而且相信自己是直言。第四,直言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别人表明真相,而是一种批评性的话语:“一个希腊人不会说一个小孩的老师或父亲在使用parrhesia。但当一位哲人批评僭主、一位公民批评多数人、一个学生批评他的老师时,这些讲者可能在使用parrhesia。”[5]最后,直言不是被迫地说,而是感到有义务去说,直言者是把说真相视为应尽的义务。
表面上说,福柯在这里讨论的不过是哲学史的某个概念。其实,福柯是在自我拷问。正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要求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一样。对福柯来说,哲学家必须是直言者,他有义务对公共事务和真相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否有危险。说真话是有条件的,有说真话的资格和能力,否则不过是闲言碎语、装腔作势或哗众取宠。凡是不符合上面五个方面的自由言说在福柯看来是有害的,它不仅会败坏私人的良心,而且会危害到公共的政治秩序。直言本质上是“向权力说真话”,直言者需要智慧和德性、勇气和义务感。同时,听众要从众多说话者中识别和认出说真话者,并且愿意相信他说的真话。前者是对说话者的要求,后者则涉及一个社会是否存在着真相生产和传播的体制。在政治学意义上,社会共识并非是对真相本身内容的共识,而是对说真相者和真相表达方式的共识。
福柯关于直言的讨论当然不可能照搬到今天。
今天不再是哲人时代,而是大众时代,真相的揭示和传播主要依赖于公共传媒、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投身于正义的社会活动家。当前出现的后真相现象突出表现为大众对精英或主流媒体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是社会进入后共识时代的结果。今天人们关心后真相问题并非是要告别真相,而是重建真相政治的基础。如果这种重建是可能的话,真相必须能够被揭露,而且真相能够塑造公共意识。今天西方在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我们知道,人们所说的真相几乎不是亲身经历的,相反,它们几乎都是通过媒体获知的。真相是否能被发现,或被认真对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报道真相的体制、机构、人员是否被信任,但今天恰恰是在这里出了问题。我们还想强调,对真相体制的信任也不是最终的东西,它是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信任的累积效应。从此次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竞选中出现的后真相现象可以看出,其最终根源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态度已经两极化了。因此当华尔街的经济精英、硅谷的技术精英和大学的知识精英还在想用真相影响选民时,选民的反应是:为什么要相信!
在某种意义上,后真相现象是西方社会共识解体后形成的犬儒主义心态普遍流行的反映。按照斯洛特戴克的定义,犬儒主义是一种启蒙了的虚假意识, 自我反思被当作自己保护的工具,对事实的肯定与否定不是根据最好的证据,而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因此,在根本意义上,真相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没有社会共识就没有经验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社会秩序能够产生出可接受的普遍后果,满足人们的公平感,产生出必要的社会共识,后真相现象才能得以克服。这一结论既适用西方,也适用于中国当下现实。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曹卫东译. 灾难与教训——短暂的20 世纪:回顾与诊断. 后民族格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9-60.
[2] Maurizio Lazzarat.The Making of Indebted Man. Semiotexte,2012:29.
[3]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常晅译. 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1.
[4][5] Michel Foucault,郑义凯译. 傅柯说真话. 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5:51、55.
后真相与历史书写
孟钟捷
当“后真相”日益引起人们关注时,它与历史学之间的张力似乎也变得明显起来:历史学是一种“求真”的学问,而“后真相”这一本质上违背真相的行为,看上去是与历史学的追求针锋相对的;进一步而言,充满着“后真相”的当下,如何在未来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呢?这些焦虑感迫使历史研究者直面“后真相”所带来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上的挑战。以下,笔者根据自己的一些理解,就“后真相”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尝试做两点评述。
第一,无论是“后真相”本身,还是预料之中由“后真相”所产生的历史书写之挑战,事实上对当代历史学而言,其实并非一个新问题。在历史学的术语体系中,作为前缀的“后”并不陌生,如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后冷战等。这些“后”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指时间顺序,表示“之后”的意思,它本身并无价值判断在内,如后工业、后冷战;二是指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表示批判的意味,如后现代、后殖民。“后真相”更大程度上指向第二层意义,即“真相”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其中延伸出来的问题至少包括:真相真的存在吗?谁为真相负责?我们能揭示真相吗?知道真相有什么意义吗?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自20 世纪中叶以来,作为历史学重要支点的“历史真相”,其实早已持续性地面对多个方面的巨大挑战。
首先在学术上面临后现代理论对真相的拷问,例如来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概念,揭示了历史研究者在认识与阐释所谓“历史实在”时的主观性,从而似乎让历史认识再也无法再现或逼近真相。当然,在这一点上,海登·怀特的本意并非是想否认“真相”的存在,而是如其所言“,我要‘解构’专业的‘客观性’的正统,并显示历史研究的核心不可挽救的是意识形态的”[1]。
而来自意识形态或政治层面上对于真相及其表述的影响,恰恰是“历史实在”遭遇到的第二层挑战。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启发,新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者致力于揭示19 世纪后历史学家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大量的个案研究发现,民族的“种族化”与“神圣化”几乎成为全球各地“书写民族”的范本,只不过基于不同的客观情势而显示出彼此迥异的解释:在欧洲,民族的单一化被视作“种族主义”的固定表达;但在南美,如巴西,“三种族联合体”同样被阐释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与这种深受民族主义运动影响下的历史叙事类似,所谓“东方主义”视角下的真实性,在萨义德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看来,不过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表达,很难说真正再现了东方历史。在女权主义兴起后,历史学者才开始关注历史上被遮蔽的女性。同理,民权运动促使人们去揭示黑人、土著等少数族裔被淹没的历史。由此,人们看到了一种持续性的“历史之战”:各种团体(政治、族裔、性别、区域等)都竭力在当下的主流历史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希望通过争夺历史话语权,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它反映的是历史书写权力的民主化所带来的碎片化特征。
最后,上述碎片化特征又由于大众传播与社会公众对历史文化的广泛参与性,而变得进一步复杂化。历史书写的职业化曾被视作历史作为一种“科学”的特征之一。它表现为训练方法的可重复性(标准课程、研讨班)、研究方法的可印证性(考证)、交流平台的固定性(期刊、学会、学术会议)。在此基础上,历史学完成了“自我理解强化”的学科化的最后阶段。但伴随“历史热”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历史日益成为公共交流的重要话题。非专业历史书写者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侵蚀着专业史学家们的话语权。他们采用了专业历史书写中不太常见甚至拒绝使用的一些策略,如爆炸性的题目(“揭秘”“与教科书不同的历史”“你不知道的历史”)、极为鲜明的倾向(支持或反对)、简单复制性的传播(造星运动、网络营销、微信推广)、浅显易懂的文字(甚至契合读图时代的需求)、煽动性的所谓民意调研(网络投票)。在这一点上,“后真相”恰恰反映了竞争性历史记忆建构中的传播策略差异,即所谓“谎话千遍成真理”与“谎话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真理”的两种态度,在历史书写中的对峙。
第二,“后真相”的出现,也为历史学本身增添了进一步反思历史与事实之间关系的新角度,特别是如何回应上述三大挑战的策略性方法。
首先,在回应后现代“真相观”的基础上,探讨“后真相”出现的历史文化品质。有关后现代史学观念或所谓“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的争论,此处不赘。但人们可以发现,在记忆理论的引入后,史料的内在视角和叙述结构越来越被研究者所重视。换言之,历史学家们已经承认,有关“过去”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具有主观性色彩的“记忆”的基础之上。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实在”,研究者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去认识这些“记忆”及其产生的进程。
由此,我们发现,“后真相”也是一种记忆。它属于某类偏见的再现。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后真相” 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大行其道?为什么一部分人对“后真相”的信任远胜于“真相”?这些问题促使历史学去思考“后真相”所产生的进程,或生产这种“后真相”的历史文化之品质。所谓“历史文化”,指的是“历史知识出现在社会中的各种形式的整体”,它是“历史意识在社会生命中作用的结合”,是“根据当下对其过去进行诠释”的模式。换言之,一个群体或社会的“过去”都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在一定文化情景中被创造出来的;任何有关“过去”的叙述或呈现都反映了各种象征性关系之间的纠葛。据此,“后真相”反映的是二战后多元主义历史文化建构进程中的“逆流”现象,即人们不再愿意“政治正确”——在民权运动压力下的族裔平等、在阶级斗争压力下的劳资和解、在女权主义压力下的男女对等——转而去支持所谓“心里话”的表达。
当然,在这一问题上,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区别“百家争鸣”和“后真相”。在理论上,争鸣被视作不同观点的碰撞。百家争鸣是社会和学术讨论的基本要求。参与者在学术规范上“求同”,在具体观点上“存异”,目标是理清事实真相,彰显多元价值。与此相反,“后真相”通常也以“一家之言”的形式出现,但其目的是为了凸显某一权威表达,反映的是一部分具有根深蒂固偏见者的历史记忆。
正因如此,历史学对“后真相”的应对,除了驳斥错误观点的谬误外——纠正偏见,理应更进一步地去思考产生这种偏见的历史文化品质:哪一部分人拥有这些偏见?他们为何坚持“后真相”?他们使用了哪些方法来彰显其观点?
其次,在回应政治权威对于“真相”的塑造基础上,探索破解“后真相”的方法。事实上,尽管真相无法完全再现,但当代史学仍然相信可以利用一些系统性方法和多元证据来“逼近”真相,例如冷战国际史研究长久以来所强调的多国档案比较研究。在这一层面上,破除“后真相”或许并不难: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时空限制,即过了一段时间、换一个角度就会出现变化;其本质不是无解的“罗生门”。为此,人们需要提供多角度的认识来应对某些特殊群体的“偏见”;更重要的是,不仅在中学课堂里,更要在社会层面上,着意培养一种多视角的历史意识,来自觉地防御“后真相”袭击。与此同时,人们用来反“后真相”的“真相”,仍需系统性和多元化的论证及展示,以防演变为(或被感受为)另一种偏见。
最后,在回应传播把“真相”复杂化的基础上,寻找提高历史文化品质的可能性。新世纪以来,公众史学与历史教育学的发展正是为了培育超越学界和面向公众时,历史传播所需要的技巧及手段,同时也为我们分析历史文化现象提供了一种尺度。德国历史哲学家吕森曾把历史文化的建构分为政治、认知与美学三个维度,分别指代集体认同策略、历史知识生产策略与历史表达的诗学及修辞策略。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在三个维度达到平衡时,历史文化才会呈现出所谓“好”的品质。而“后真相”则是以贬低认知维度为代价,通过凸显政治维度或美学维度的方法, 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作为抵制“后真相”的历史书写,自然需要在其他两个维度上加以修正和强化。在这一方面,专业历史学者走出象牙塔,更多面向公众进行历史写作,或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
总而言之,在历史研究层面上,针对“后真相”,历史学能够采取的策略是:承认真相的复杂性,对事实加以系统性、规范性和反思性的研究,最终形成批判性的历史诠释。当然,倘若“后真相”超越了民族国家范畴,进入到不同场域之间,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历史之争”——例如二战历史记忆,则需要多国历史学家跨出民族主义的界限,携手祛魅,寻找共识。
参考文献:
[1] 姜芃. 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4.
修辞术博弈:
“后真相时代”的政治传播症候
陈龙
2016年的美国大选,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极度反常的政治环境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后真相”世界的兴起——几乎所有权威的信息来源都遭到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事实的挑战。特朗普上台前后各种真信息、假新闻混杂在一起,所有政客都为自己的利益而编造谎言,歪曲事实,轮番上演着现实版的《罗生门》。“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一切不可能都成为可能。“Twit ter 治国”渐渐被鼓吹成一种世界政治潮流。社会正义、法律秩序、媒介公信力等似乎变得不再重要了。社交网络成为代表“人民”的媒体,并在反对“政治正确”中具有了天然权威。“代表民意”的特朗普,在Twitter 上用“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鼓动民众情绪,引发情感认同。此时,“来路不明的事实”已成为一种政治武器,“这本身就糟糕透顶”[1],社交媒体容易高点击率、高存在感,但公信力却频遭质疑,“黑天鹅事件”不断出现,各种“真相”“事实”迷乱人眼。于是,说谎成了“后真相时代”的一门艺术,“包装事实”在无把关人的社交媒体空间泛滥,个个都竭力抢占舆论先机,目的是争夺话语权。
在民粹化风潮中,人们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公信力丧失对社会的危害,这正是社交网络中潜藏的风险。“包装事实”本质上是一种古典修辞策略,然而在当下却成为一种政治症候。纷乱的修辞竞争,正是利用了社交网络表达的意见自由市场体制,混淆了真相和假象,最终实现浑水摸鱼的效果。修辞术博弈成为“后真相时代”的常态,这在中国的社交网络空间也客观存在着,既有与欧美相似的表现形式,也有自身的个性特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迫在眉睫。
“后真相时代”修辞术博弈实质是话语竞争
社交媒体技术提升了信息传播的自由度,带来了海量的信息,带来了表达和交流的自由,任何人理论上都可以在社交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表现在政治传播中,其优势明显体现出来。新媒体政治传播与传统媒体时代有着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传统媒体竞争基本是媒体内容或通过发挥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为公众设定议题,但传统媒体有一个道德底线,那就是不能发表虚假新闻,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约定俗成,虽然也有偶发虚假新闻个案,但总体是有“把关人(gate keeper)”存在,核查事实真相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社交媒体时代,“把关人”这一重要角色没有了,一个“把关人”缺席的媒体,其功能已经转型为一种平台,类似于转盘式的餐桌,谁都可以往上放东西。走过早期互联网阶段,社交媒体的政治潜能被挖掘出来,既然网络可以实现对观点的自由表述,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反馈将会非常便利和迅速,那么从此他们就可以更少地依赖新闻机构、利益集团、专家、官员和精英,所有的意见将产生于他们自身。
古典修辞学所强调的修饰文辞以达到最佳演讲效果的理念,在社交网络时代有了很大的用武之地。古典修辞学将影响受众作为终极目标,其手段仅仅限于修饰文辞。而在今天的互联网社会,修辞术的核心要义是看能否争取广大网民。在当下,无论古典修辞学还是新修辞学均将假新闻作为争取受众的“修辞术”,其危害难以想象。美国苹果公司CEO 提姆·库克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示,“假新闻正在杀死人们的思想”,可以说是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在“吸粉”成为竞争性工作的背景下,民粹主义很自然地成为修辞术运用的道具。在这里,民粹主义把个人看作是缺乏联系的原子化个体,而社会不过是有着地理边界的这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仿佛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将社会普度到一个境界,个人价值从此得到高度的凸显。因此,网络空间在他们看来就是真正民主运动的场域,而网络传播就是典型的政治实践。[2]
中国社交网络空间的政治传播实践,从本质上说就是话语竞争。然而,有别于传统媒体时代信源真实的有序竞争,社交网络时代的竞争更多的是无序竞争,其最大的特点是用虚假信息参与话语竞争, 话语修辞的出发点通常服务于各种政治势力和各种政治诉求。各种标题党、各种耸人听闻的帖子、“真相”图片,远不是“假新闻”的危害那么简单。可以说,新媒体空间的修辞术说到底就是江湖术士的“骗术”,各种刷存在感,刷屏竞争,目的是获得话语的主动权。“真相”有没有变得不重要了,各种伪装“真相” 最容易蒙骗不了解情况的普通民众。按照美国学者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的描述,一件危及所有人生命的核事故发生了,各种渠道关于这一事件的新闻即刻潮水般涌来:“传统新闻网站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呈现碎片状,而且常常自相矛盾。各类消息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在不同的网站得到的讯息完全不同,甚至如果在不同的时间访问同一网站,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3] 用虚假信息参与话语竞争,这种传播的修辞策略服务于参与政治角力的势力,越来越成为社交网络时代政治竞争的常见手段。
后真相时代修辞术博弈是劝服传播的堕落
“后真相时代”或者“后真相政治”一词,是美国传媒学者兼畅销书作家拉尔夫·凯斯(Ralph Keyes)最早提出的,凯斯敏锐地发现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选举政治的新动向,这种变化就是通过网络舆论操控或影响民意。梳理一下互联网发展历程便可知,起初,人们认为互联网是上帝的“恩赐”,它带来的是民主政治的愿景,它给人们带来海量信息,也让人们无限接近事实真相。告知传播、自由言说是这种媒体的突出优点。然而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仅仅用了不到 20年时间,这种愿景就被无情地打破了,很快网络传播便实现了由告知传播向劝服传播的转型,转型的结果更多的类似于二战期间的宣传(propaganda)——不择手段地诉诸情感认同。
二战时期,宣传是劝服传播的一种极致,意味着为达到影响受众的目标而不择手段。当信息转化为一种武器时,修辞就成为必要手段了,如何增加话题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这需要将所谓“真相”纳入某种框架进行叙事。一个戏码,多种脚本。在欧美国家,这种戏码无一例外都是民粹主义式的,各种脚本都包装成底层大众的话语,批评现有体制、精英和“政治正确”。在中国的网络空间,这种戏码的叙事表现为“三仇”,即仇官、仇富、仇专家[4]。诉诸情感而不是诉诸事实,这在中国网络空间司空见惯。选择民粹主义的议题进行渲染,正是玩弄修辞术的表现。
劝服传播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27 年拉斯韦尔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在政界和学界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带有教唆性质的著作,建议“马上销毁它”。这反映了当时人的普遍心态:对“宣传”的功效充满恐惧,有明显的厌恶感。
20 世纪30 年代经济危机后,劝服传播广泛应用于广告领域,其通常的方式是借助于艺术化的手段,将广告商的产品、服务推销给社会大众。劝服传播关注的是效果,即传播内容是否打动了受众。当下劝服传播的特殊性,在于修辞策略进入话语场角力、竞争,其结果导致谎言成为艺术。这样,江湖骗子有了参与政治竞争的机会,并且有很高的获胜几率。[5]
作为劝服传播的手段,修辞策略可以有多种常见表现形式,散布假消息、贴标签、巧妙“借用”、省略、渲染、权威发布、标题党,等等。谎言可以借助技术的包装,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当下“算法崇拜”“大数据崇拜”的背景下,某些特殊事件节点的
“发布”就带有很强的修辞意味。社交媒体、大数据天生携带着民主化媒体的神圣光环,决定了民众对它们的信任度。然而,种种基于社会大众心理,使用修辞策略包装出来的民意最终将导致何种结果,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法西斯的抒情诗”不无道理。[6]
劝服传播堕落后形成的舆论流程发人深思,无论是夸大、歪曲还是有意忽略某些重要的事实,都会助长愤怒、恐惧和憎恶的情绪。社交网络空间中的假新闻,在反转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二波制”信息传播格局:第一波,某个信息发布,往往先抢占道德话语制高点,受众激情澎湃为某个人物或事件悲悯、同情、欢呼、痛恨……第二波信息对前一信息进行辟谣、反转,新的信息推翻了前述事实,证明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彻头彻尾的狗血剧。这些都是劝服传播竞争的习惯性模式。
“网红”式政治是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异化
既然社交媒体具有天然正义,人们认为真相存在与否不重要了,情感的感染力、思想的说服力才是最重要的。例如美国大选,除了少数传统媒体还延续传统路线,查证信息的真伪,监督竞选人的言辞是有理有据还是随意编造,更多的媒体和观察者热衷于鉴赏“金句”,看是否一句话就能把对方打趴下。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在观看一场辩论戏剧, 而不是事关国家前途的政治头脑风暴。这渐渐成为“后真相时代”的西方政治风景。西方选举政治的新趋势,与传统的大选看点不一样,竞选的方式和内容都相应发生了变化,与传统的“真相时代”形成反差对比。以往人们参与大选或者全民公决,主要看参选人说的是不是事实,说话有没有依据,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合乎情理。而在“后真相时代”,参选人追求的是吸引眼球,设法用雷人雷语等方式,靠拉近选民的感情来获胜,打的是“ 感情牌”。至于说话是否有理有据,政策是否可行,都成了第二位的。
这样,政治选举蜕变成网络红人式的选秀,选民演变成粉丝,他们更多关注的就是候选人的“表演”,即便是丑闻也可能聚集众多粉丝,能否吸引媒体关注和热议远比解决国家面对实际难题要显得重要。于是,胜败的主要因素不是政治家的品德和远见,竞选的核心不是谁的政见高明,谁能惠及国家和民众, 而是看你能不能抓住多数选民的感情,哪怕枉顾事实,哪怕信口开河,把对方抹黑把自己描红,只要能“吸粉”就是成功。欧美国家的选举风情表明,选举的结果离选民的初衷相去甚远,一个善于表演、善于发布雷人雷语的“网红”替代了人们心目中的政治家。新媒体将政治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对传播效果的追求,导致修辞术泛滥,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发生了异化。
新媒体技术在本世纪的诞生,带来了对传统社会规则的改写,毫无疑问,新闻传播的规则也被改写了。这种变革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人们普遍获得了信息的采集与发布权。然而,在自由发言过程中却没有建构起其应有的秩序和规范,尤其是对于恶意宣传式的新媒体传播内容缺乏治理对策,最终导致网络空间修辞泛滥、各种欺骗手段盛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破坏性。它颠覆了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秩序和规则,由于在民众心目中具有传统媒体不具有的“天然正义性”和“天然权威”,对底层社会往往蛊惑能力更强,更具有迷惑力。可见,“网红”式政治对社会的危害,正是政治传播异化的表现。
后真相时代修辞术或江湖骗术在政治传播领域的泛滥,渐渐成为常态。在社交网络空间,各种“抹黑”“扣帽子”行为很明显都是谋求对事件性质的定义权,而这种定义霸权是典型的专制性修辞术,其终极目标是争夺话语权。后真相时代修辞术盛行是一种社会症候,其病态根源应当从社会的内部寻找,这应成为社会治理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1]弗朗西斯·福山“.周刊,2017.2.13.
[2]陈龙、陈伟球. 网络民粹主义传播的政治潜能. 山西大学学报,2012(3).
[3]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 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信什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
[4]陶文昭. 中国民粹主义的“三仇”“两求”与“两过”.人民论坛,2015(5).
[5] Paolo Davoli,Letizia Rustichelli & Francesco Tacchini.The Birth of Digital Populism:Crowd,Power and Post-Democr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Obso- lete Capitalism online,2014,Preface(XI).
后真相政治探幽
王金林
“Post-truth(后真相)”,这个《牛津词典》精选的2016 年年度词果然热度非凡。最近大西洋两岸分别开会 ,后 真相均赫然在列。美国纽约举行的学术会议专论后真相,而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则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为主题。后真相一跃而为诸后之首。后真相是何方神圣,如此大热?这当然同2016 年国际政治中所发生的两大黑天鹅事件有关:一是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力压留欧派,英国脱欧成为定局;二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政治极不正确”的特朗普大胜老牌政客希拉里,逆势入主白宫。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的潮流似乎正在席卷英美。后真相这个术语正是在此背景下跃然而出,被用来勾勒当下西方政治的新生态。《经济学人》杂志2016 年9 月发文《谎言的艺术》, 探讨后真相政治何以诞生。《纽约时报》网站此前亦载文《后真相政治的时代》,径直以“后真相政治”来命名当下时代。
考诸英国脱欧公投与美国总统大选这两大后真相政治实例,人们不难发现,后真相政治的特点,首先在于把真相后置,如英国脱欧派一再声称欧盟成员身份让英国耗费巨资,却无视英国所获的利益;其次在于干脆信口雌黄,完全捏造事实。因此不妨把后真相政治规定为:A. 在形成民意方面,相比情感与个人信念,事实或真相无足轻重;B. 倘若需要,可以直接捏造事实或真相。
但是,必须承认,这两种现象在政治传统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为政治利益计,政客们经常轻视或捏造事实,这司空见惯,了无新意。但以往的经验是,政治谎言一旦暴露,撒谎者代价不菲,引咎辞职者有之,身败名裂者有之。后真相政治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虽然置事实于不顾,虽然谎言已被揭露,后真相政客们却可能无须付出道德与政治代价,反而往往人气爆棚,逆势而上。这就非同寻常了。因此,后真相政治的第三个特点在于:C. 谎言败露却无政治代价,反而可能大获政治红利。后真相政治之新奇正在于此!肆意妄为不受惩罚,厚颜无耻坐收渔利;撒野撒出了新境界,煽动煽出了新时代。这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这可能是二战后西方政治面临的最大的内部挑战。人们不禁要怀疑:西方政治文明是否正在退化?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否正在卷土重来?
后真相政治兴起的动因
后真相政治固然荒唐,但其悖然而兴的动因却有迹可寻。首先,全球化为后真相政治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阵营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蔚为壮观。一时间,资本、技术、物品、人员乃至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加剧流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国家体制的限制与社会再分配机制的滞后,全球化无论是在国际层面上还是在国家内部都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单就国家内部而言,全球化的红利主要由精英阶层攫取,中产阶层所获甚微,劳工阶层更是频遭重创。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中产阶级朝不保夕,数量大幅度下降, 如美国的中产阶级就从危机爆发前的总人口占比70%下降到不足50%。这在西方国家内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后果。后真相政治只是其中诸多症状之一。
其次,乘势而兴的民粹主义直接催生了后真相政治。经济全球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化,左右翼民粹主义应运而生,并且右翼势力要远远大于左翼势力。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有诸多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声称真理不是掌握在精英手中,而是掌握在草根手中,因此必须以“草根对抗精英”的模式,摧毁整个社会建制。这些运动当然不无现实的正当性,是对资本导向的全球化的抗议。但是民粹主义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则结果难以逆料,对现代文明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当初希特勒就是在一股民粹主义旋风中强势登场的。民粹主义凡事诉诸情绪而不是事实,虽然那些情绪本身有其经验基础。民粹主义政治主张虽然五花八门,但都有一种立场先行于事实的非理性特点:事实必须服从于立场,服务于立场。民粹主义正在造就后真相政治之特性。
最后,社交媒体为后真相政治之兴起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全球化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好,民粹主义的分裂鼓噪也好,倘若没有社交媒体所提供的空前的传播力,都不足以在足够庞大的规模上汇聚成一种后真相政治。社交媒体的流行使事实来源多元化,每个用户都可以就任何问题对整个世界发声,不管他是否了解真相,是否愿意透露真相。不同的渠道有着不同的诉求,不同的诉求有着不同的利益,事实或真相往往在众声喧哗中隐而不显。后真相意味着事实本身的危机。事实由谁来发布? 机构与专家对事实的垄断在互联网时代日益岌岌可危。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人都可发布事实,表达观点。人们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相互巩固。主流媒体乏人问津,社交媒体热闹非凡,流言不胫而走。别有用心者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或无视真相,或捏造事实,一切以自己的情绪与利益为准。反特朗普的IT公司如脸书与推特居然因谣言满天飞而客观上帮助了他。特朗普本人则在推特上一再发布掺假或完全虚假的事实性陈述,被揭穿后却仍然气壮如牛。这在前社交媒体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后真相政治的兴起,还有更深远的思想理论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就思想理论而言,后现代理论恐怕难辞其咎。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后现代话语不遗余力地攻击现代宏大叙事,解构现代性及其所包含的几乎一切立场、观点与方法。在后现代话语中,真理、意义与价值被解构得体无完肤、千疮百孔。对于建立在现代存在论与认识论基础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来说,求真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现在在后现代潮流的冲击下,事实或真相危如累卵,难以为继。后现代理论掏空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哲学根基,为后真相政治的兴起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就社会文化而言,各种认同文化或认同政治的兴起对事实或真相的瓦解效果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譬如,从同性恋公开化到同性婚姻合法化,西方领头羊美国在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在人类最基本的性与婚姻制度问题上走得如此之远,如此之激进,令世人惊讶。这在社会文化层面上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波: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没有什么是可以依靠的……美国大选期间,有位投票给特朗普的老年女性曾非常困惑地对记者表示:为什么我们年轻时的一切错事,现在却都对了。这话发人深省:认同文化是否走得太快太远了,甚至误入歧途了?在类似令人纷扰的情绪中,人们很容易相信价值与事实本身就不可靠,只能依赖自身的感觉与情绪。在后真相政治起因上,认同文化及其社会实践显然难脱干系。
后真相政治的危害及其应对
后真相政治的危害已经初露端倪。择其要者而言之,首先,是事实危机。真相后置造成了后真相政治。后真相政治则反过来加剧了事实危机。民众在后真相政治中不得不漂浮在谎言海洋中,无所依靠, 退化为受情绪或情感主宰的“后真相动物”。感觉当道,事实何存?在后真相时代,一直受制于理性的感觉似乎被彻底解放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当代社交媒体正好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手段,让感觉的野马狂奔不止。韦伯所谓的社会理性化过程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其次,更严重的是政治危机,民主制遭遇严峻挑战。政治面临着再野蛮化的危险,可能重返赤裸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民主制归根到底要以事实为最后诉求。在形成民意的过程中,倘若事实无足轻重,甚至被完全无视,则民主制的事实根基就整个动摇了。其后果势必导致政治文明的倒退。政治一向以克服自然状态为目的。现代政治经过启蒙的洗礼,其区别于前现代政治的关键恰恰在于求真,但随着后真相政治的悖兴,政治却被再度野蛮化。“政治不正确”的人居然凭借对“政治正确”的攻击,而当选总统,这对西方民主制而言无疑是极具挑战的。如果说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乃二战后西方政治野蛮化之先兆的话,那么特朗普就是这一趋势最新的集大成者。把他们送上台的朴素信念无非是:不管野蛮与否,只要能解决经济问题就行。二战前的德国曾经非常熟悉这一逻辑。
最后,是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政治再野蛮化造成社会共识开始分崩离析,道德底线一降再降,随时有被击穿的可能。在社交媒体上,人们不再是如腾尼斯所言“从共同体到社会”,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从社会到共同体”。当代社会进程仿佛逆向而行,正在加速再部落化或再封建化。古老的“部落械斗”完全可能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重显江湖。
后真相政治的危害令人不寒而栗。那么,应当如何应对后真相政治呢?概而言之,首先,在政治经济方面,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不稳定,社会贫富悬殊, 必然催生极端的民粹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路径必须改弦更张,否则政治极化与社会分化的趋势断难阻挡。全球化必须建立起自己有效的再分配规范与机制,防止资本的贪婪激起民粹的强烈反弹。第二,必须重塑事实与真相之权威。这就要求整个社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必须认真对待自己所发布或传播的消息与数据,并为此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民无信不立。一旦失去公信力, 社会代价非常惨重,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一个“失真”“失信”的社会必定“失范”。第三,社交媒体的有效治理势在必行。在确保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网络实名制与“信息信用制”都是可供选择的技术手段,必须让“后真相政客们”付出应付的道德与政治代价。
总之,倘若“后真相政治时代”赢得民意之关键真的在于“谎言的艺术”,而不是事实或真相,那么这无论如何都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已经遭受重创。《经济学人》文章最后假设:“如果特朗普先生十一月输掉大选,那么后真相威胁就会较少。”不幸的是,结果恰恰相反。面对甚嚣尘上的后真相政治,我们必须重申:求真乃是一条不可逾越的人类道德与政治底线。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
共享视角的瓦解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
刘擎
新近出现的流行术语,往往涵义模糊不清,也容易被误用和滥用“,后真相”或许更是如此。我们首先需要做一个简要的概念梳理。严格地说,后真相并不是一个新术语,它最早出现在 1992 年《国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自2004 年之后在美国的时政评论中被更多的作者使用。而到了2016 年,在对英国脱欧以及美国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分析讨论中,“后真相”一词迅速流行,使用频度比上一年上升了2000%,因此被《牛津词典》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
我们可以对后真相议题提出两点阐发。首先,后真相议题目前着眼于“公共意见”的形成,因此主要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在行业规范、专业学术研究等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但尚未受到明显的困扰。而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后真相的麻烦与纠纷或许屡见不鲜,但并未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其次,后真相情景并不完全否认真相或彻底无视真相,而是与真相处在一种复杂的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关系之中。在研究者列举的典型的后真相案例(比如2016 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人们并不公然否认“事实” 的存在,也不否认援用事实证据的必要性,甚至频繁地使用“数据资料”作为依据来“论证”自己的主张,因此在表面上似乎仍然“重视事实”。但另一方面,人们在公共讨论中往往被自己的情感因素和个人信念所主导,当事实真相与自己的观点发生冲突时,很少有人致力于质疑、反思、修改和调整自己既有的观点, 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在现有的数据资料中做片面的选择取舍,通过“改造事实”甚至“操纵证据”来达成自己喜好的结论。在后真相的政治文化中,人们以往熟知并承诺遵从的“从事实证据推出结论”或“结论服从于事实”的逻辑规则发生了逆转,转变为“让事实证据服从于既定的结论”。后真相时代与“事实胜于雄辩”的原则渐行渐远,而“雄辩胜于事实”的现象似乎蔚然成风。
那么,后真相状况何以会出现?造成后真相政治文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在复杂多样的成因中,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缘由都值得探究。就理论逻辑而言,真相问题是现代哲学长期未决的难题, 这为今天出现的后真相现象“留下了隐患”。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隐患),并不必定表现出实践效应(征兆)。在实践层面上,近年来全球化和新技术文明的急速发展,在欧美国家造就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促成了这种理论的逻辑可能性“显形”为具体的社会现象,哲学难题因此彰显为值得关注的政治文化困境。
尼采的幽灵与真相的哲学难题
后真相问题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最为相关的哲学渊源是一个多世纪前,尼采对事实真相客观性的挑战。尼采曾在《超善恶》的序言中写道:“视角(perspective)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而在其遗稿“札记(Nachlass)”中,他留下了著名断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这个被哲学界称为“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的观点是尼采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也为今天的后真相时代埋下了伏笔。
对于如何理解视角主义,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这再自然不过了,根据尼采自己的逻辑,我们可以说,没有所谓“真正的尼采”,只有对尼采的各种阐释)。有人认为,尼采在根本上反对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因此他彻底否定事实本身的存在。但也有人认为,视角主义可能仍然承认事实的存在,只是坚持主张,独立于视角和阐释的事实或真相是一个虚构——只有从虚构的“上帝之眼”这种全知视角才可能把握, 这是人类不可企及的,因此对我们完全没有意义。但无论如何,对尼采而言,绝对客观的事实真相要么不存在,要么不可企及,因此“客观知识”就不再可能。那么,失去了客观性标准,所有视角和阐释都没有高低对错之分吗?尼采似乎并不肯认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因为他自己反复论述,各种视角、道德或生活方式存在着高低之分——有些是高明的,值得赞扬的,有些是卑下的、扭曲的。但如何可能在放弃真相(真理)客观性的同时不陷入相对主义呢?这是尼采思想研究中令人困扰的一个问题。
视角主义与后真相问题还具有一个重要的关联线索,可称之为“视角制造事实”的思路。尼采的视角主义并不只是强调所有事实论述都涉及阐释,而阐释取决于我们的视角。他对传统哲学的挑战远比“阐释无所不在”这种通常的见解更具颠覆性。视角主义的激进主张在于,视角本身是要“创立”而不是“发现”价值的尺度,包括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什么是道德,也包括什么可以算作“恰当证据”的标准。如果所谓“事实”就是满足了“恰当证据”的事务,而恰当证据的标准又是视角所创立的,那么“没有独立于视角的真实世界”意味着“事实”,在一定意义上是视角所制造的。
“视角制造真相”听上去匪夷所思,可以用一个最近的现成例子来说明特朗普眼中美国就业率的事实。美国近8 年来的明显就业增长,被认为是奥巴马执政期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他就职之初的2009 年1月,美国失业率为7.8%。到他卸任时的2017 年1 月, 失业率降低至4.8%,达到经济学通常的“充分就业”标准。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一再强烈指控这些失业率数据完全是虚假的,使用的统计方法完全不可靠。他反复声称美国失业问题严重“,实际的失业率是28%~29%,可能高达35%左右,甚至听说是42%”。在此,特朗普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建立了自己的“恰当证据”标准,质疑了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所颁布数据的可靠性,从而制造了美国失业问题严重的“事实”。
但在特朗普上任后,最新发布的2017 年2 月的失业率小幅下降到4.7%,特朗普为此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这显示他的“新政”具有显著成效。白宫新闻发言人转述了特朗普对失业率数据的评论:“过去那些数据可能一直是虚假的,但当前是真的很低。”在此,特朗普肯定了新的统计数据,符合他现在视角下认可的恰当证据标准,从而确立了“美国当前就业充分” 的事实。他似乎完全不用理会,前后所有的数据都是由美国劳工统计局以同样的调查统计方法获得和发布。此前作为竞选者和现在作为总统,特朗普身份的变化改变了他的视角,也改变了他的证据恰当性标准,从而制造出两种不同的就业率“事实”——这是后真相风格的事实,带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神韵。
那么,真相本身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我们是否可能以及何以能够认识真相?在专业哲学领域中,关于现实世界是否存在、我们的知识是否建基于符合客观现实的反映或认识、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现实具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存在着持久而复杂的研究和辩论,形成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不同观点以及各种立场的组合,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就此而言,尼采并不是唯一的“麻烦制造者”。
当然,哲学家的难题通常不会困扰人们的日常生活。普通大众的现实感或常识观念大约来自一种朴素的本体论的“实在论(realism)”与认识论的“符合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的结合: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真相(或真理)是符合客观现实的知识,知识可以获得严格的客观性检验。依靠这些朴素的观念,人们大多可以理解自然世界的现象,也能够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因此,我们一般不必去理会尼采。病人在医院看病时不会从视角主义出发去质疑医生的诊断(我们不会说,在医生的视角中病人患有高血压,而从病人的视角看来这不是事实)。视角主义似乎与我们的常识感相悖,因为心智正常的人们确实一致同意许许多多事实真相: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冬天比夏季寒冷,商品降价有助于销售……这些事实独立于任何人的主观视角,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那么尼采对此又会作何解答?依据视角主义的观点,独立于视角的所谓“客观事实”不过是一种错觉,实际上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具有共同的视角、得出了一致的阐释, 才造成了“客观性”的感知。当代有些科学家也主张,现代科学不需要假设存在着独立于视角的客观现实。比如物理学家霍金在《大设计》一书提出的“模型依赖的实在论(model-dependent realism)”,这种观点已经放弃了古典的实在论立场,但仍然能坚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视角主义的启发意义在于,真相的“客观性”依赖于“共同视角”,如果我们大多数人能够共享相同的视角,那么作为“合理幻觉”的客观性仍然能够维持。就此而言,好消息是,人类在许多问题上分享着共同的视角,由此达成的共同阐释可以作为“客观事实”被接受;但坏消息是,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并不总是具有共享的视角,一旦彼此的视角存在严重冲突, 仅仅诉诸事实真相对解决分歧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真相本身恰恰是分歧的焦点之一。此时,尼采的幽灵会浮现出来,视角主义的理论逻辑会彰显其实践性,成为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困境,这或许正是2016 年欧美国家政治变局的状况特征。
视角分化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
现代性与多样性往往是共生现象,在充分现代化的欧美国家,社会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不仅程度更高,而且具有更复杂的多重维度:种族、职业、性别、居住地、教育程度、经济阶层、宗教信仰、文化身份和价值取向等。这些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利益感知、道德态度、认知方式和情感结构等,构成了人们的视角。这些维度的极端差异会造成视角的严重分化, 导致在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问题上社会共享视角的削弱乃至瓦解,这促成了后真相时代的来临。而社会世界的事实比物理世界的事实具有更强的理念建构性,也因此对于视角的差异更加敏感,更容易导致对何为真相的阐释分歧:全球化推动了经济发展吗?美国硅谷的从业人员与中西部“锈带”地区的工人,对此可能做出不同的真相判断。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为因素造成吗?煤炭、石油行业的企业家与新能源企业的创业者,可能会诉诸不同的“事实”证据。人工堕胎实际上是杀害生命吗?基督教徒与非教徒之间可能发生意见冲突。穆斯林移民与人口增长将会颠覆西方文化传统吗?左翼知识青年与文化保守派人士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阐释……
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技术条件所造就的传播环境。在更早的时代里,公众意见的多样性难以充分表达,主流媒体的权威声音可能通过排斥和整合,控制多样性的程度,达成某种基本共识。而共识效应又反过来发挥了限制视角分化的作用。当今网络与社交传媒的发展,创建了崭新的交往与传媒方式,公共发言几乎不存在任何的门槛,“随便什么人对随便什么问题都可以随便地说些随便的话”。公共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众说纷纭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传统知识权威的衰落,却未必能促进开放和理性反思的公民政治文化。网络传媒依据特定的个人浏览偏好,通过“算法”自动推送相关内容,以及社交媒体朋友圈的“回音壁”效应等,都倾向于固化人们既定的价值和观点,从而使同类人群更加固执己见,同时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视角分化。新的传播与交往模式也是造就后真相政治文化的成因。
后真相状态呈现出一种深刻的挑战:我们以往长期信奉的公共交往原则和规范——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真相面前人人平等,都不再是自明正当的,也不再能够有效地应对公共意见的分歧。共享视角的瓦解将会使民主政治陷入严峻的危机。大多数政治理论的研究表明,现代民主政治要求公民肯认最低限度的共享价值和政治规范原则, 这在根本上需要在公共文化中养成。否则,民主制度的程序无法有效地运转,或者蜕变为压制性的权力机制。如何重建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共文化,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艰难任务。就此而言,对视角主义本身的不同阐释,可能带来不同的前景。
如果以教条主义方式来解读,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那么固执己见和无休止的分歧将是宿命性的后果。但以教条主义来解读尼采,这本身是巨大的讽刺。我们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从尼采的洞见中获得启示:恰恰因为“上帝之眼”的视角不再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视角只是众多可能的视角之一,这使得谦逊成为必要,这邀请我们向其他更多的视角开放、倾听、理解和学习,这在我看来也是尼采本人赞赏的态度。正如他在《道德谱系学》中写的那样:“我们越是知道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是如何打量同一个问题的,那么对此问题我们的‘概念’以及我们的‘客观性’就越是会完整得多。”[1]个人视角并不是“给定的”,而是形成的。虽然视角的构成要素相当复杂,改变也不容易,但不是凝固不变的。自我视角的转变、跨视角的移情理解以及不同视角之间融合,虽然这总是困难的,却也总是可能的,这在后真相时代比以往更加重要和紧迫。这种可能性蕴含着重建公共文化和应对后真相政治困境的希望。
参考文献:
[1] Friedrich Nietzsche.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Maudemarie Clark and Alan J. Swensen.Hackett Publishing,1998:85.
后真相世界的民粹化现象及其治理
邹诗鹏
“后真相”是一个很具穿透力和表现力的称谓, 也形象地描述了当下时代的某些症状,属于后的描述之一种,很典型。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会前报告,一连用了三个“后”,即“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且以“后真相”打头,引人注目。不过,相对于后真相时代这一有些夸大其词的称谓,我更愿意称为“后真相世界”或“后真相现象”。而本文所关注的,是后真相 世界在政治与公众生活方面的民粹化现象。
后真相世界及其民粹化现象
应当说,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已经揭示过所谓“后真相”现象:“考虑事物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更重要,因为只有它们,是我们能看到并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1]看上去,勒庞揭示了后真相现象的认识论基础,但他没有考虑到:种种有意回避或不说出真相的犬儒主义,才是后真相现象的社会心理基础。我们今天面临的后真相现象,并非不承认真相的存在,而是被种种后现代价值预置了的世界景象。
后真相显然是主观化的结果。后真相的特征在于,情绪与感觉远比事实与真实更重要,不是实事本身,而是情绪化和感觉化了的社会事实,甚至散布于网络世界的流言、谎话、绯闻,其意义都比真相重要。真相的次要性,显然是相对于大众的情感及其接受心理而言的。人们的行为是被话语而不是事实所支配,整个社会系统更加依靠社会心态及其承认程度。在网络世界中尤其如此,在那里,任性的个体及其对认同的抵制,直接加剧了网络民粹化。正如卡斯特所言:“网络社会的抵制认同,像从前曾经构成工业时代公民社会的合法性认同瓦解时产生的个人主义方案一样,到处可见。然而,这些认同相互抵制,它们很少沟通。除了为了他们特殊的利益/价值而抗争与谈判之外,他们不与国家沟通。他们很少彼此沟通。”[2]网络社会的离散化趋向显然加剧了民粹化。
后真相世界是一个新闻化和网络化的世界。显然,作为主观化的结果,后真相世界又是真实而客观存在的现象世界。后真相并非指不存在或不承认真相,而是指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即使我们认为存在并承诺真相,我们也已经置身于各种铺天盖地、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信息、图像、拟像乃至于乱象的世界中。真相的确就掩藏在这一表现性的世界中,以至于要抵达真相,就不得不放弃求真而放任于各种表象世界。在这一意义上,后真相意指发现真相的无力、无能及不可能。后真相世界默许的价值观,就是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则是其极端形式,但后真相现象的土壤及其典型症候,还是民粹主义。因此,如果说福柯还在承认并寻求“求真意志”并因而肯定世界的真相,那么,鲍德里亚讲的拟像化则直接承认了后真相世界,并因此洞穿彻底的虚无主义。但彻底的虚无主义是后真相的极端形式,我们关心的还是后真相世界背后的民粹主义,应对民粹主义,是避开虚无主义的有效途径。
网络社会的后真相化及其民粹化现象分析
后真相的主因,乃是网络世界中真相湮灭于无限扩展和增值的表现性话语,以至于无法呈现和还原。与传统时代民众有限的公共生活参与度不同, 网络时代,人人都是事件的主体且人们只愿意接受自己看到的世界,网络大众的情绪、意见直接参与并不断改造和重塑公共话语。与此同时,世界的高度“事件化”使得还原每一个事件的可能性减少且不必要。“真相”随事件性而来,其不断延迟,同时也在分解,或不断出现新的真相,而聚集及其事件化又以自身的力量拒斥真相,莫衷一是。
网络世界的“后真相化”,其实质还是网络民粹化。“后真相”导致聚集状态的复杂化和无序化,不可小觑。设想一个场景,街头,两只虫子扭在一起,此时围上几个看热闹的人,接着好事者越来越多,后来围上来的人们已不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而只是往上围,但人群中已经开始流传各种版本的“真相”,越传越神,也就越有人信,“真相”就出来了,甚至于上了当天的小报。在这里,大规模并且群情激奋的聚集,直接取代两只虫子而成为事件的真相,尽管聚集本身依然不过是无聊的和偶然的街头性事件。现在,网络上成天充斥着的正是这类看上去热闹、实际上很街头甚至于很狗血的事件。只是,网络社会的街头化比比皆是,微信交往其实就是人的街头化,伴随着趣味的离散与时间的碎片化,必定是巨大的信息与事件世界,但事件性往往在其尚未经得起推敲时,就已经让位于匆匆而来又转瞬而逝的另一起事件,这里,并非真相而是热度(或噱头价值)决定着事件之成为事件。人们被消费游戏于过眼烟云般的信息世界,实际上早已无需辨明或值得辨明信息的真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真正的事件,也难免成为网络热炒的噱头。其实,后真相世界就在不断扼杀事件的历史性。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但是,“吃瓜群众”恐怕并非旁观者,自媒体时代没有旁观者,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而且,“吃瓜群众”未必追求真相,边吃着瓜,边编发微信,事件就这么制造出来并传遍天下和蛊惑天下,所谓“看戏的不怕事大”,不明真相却创造“事件”。后真相世界当然是事件频频出现而真相隐退的世界,推动者正是不明真相的网络大众,换句话说,网络大众追求的是情绪的表达与宣泄,而并非“真相”。事件才是网络时代的真正联结点。事情的事件化是人们话语实践的结果,事情越是事件化,真相越是隐蔽起来。真相敞开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求真意志,而是取决于话语中止的可能性,但“看客们”的“好事”心态实际上早已淹没且阻止了求真的意志,剩下的便是“后真相”。
追求并敢于说出真相,在传统时代被视为美德,在那里,富于政治勇气,是英雄主义的表现,并因此拥有群众收获民心。但是,网络时代,真相让位于激情,且已不那么重要,追求真相则显得落伍和多余, 有时甚至会被看成是伪善者。此时,顺着大众激情而发话者,哪怕他采用的是势利逻辑,也会拥有大众,相反,立足于精英立场反倒被视为小人,特朗普与希拉里,代表的仿佛就是上述两种路数。不过,希拉里未必真的在意真相,她同样在意表演性政治。只要有必要,势利者特朗普同样也会无视真相,事实上,正是他成功地利用了大众因民粹化而陷入的后真相状态。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后真相世界里,大众才是表演性政治的主体,而政治表演者则经常是玩偶。
网络民粹化的治理
对后真相的无奈表明当下时代政治对网络民粹化的迁就,也反映了治理网络民粹化现象的艰难。
传统时代的政治思想格局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大主流政治谱系及其对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应对传统,主流政治对民粹主义的应对表现为真相政治以及理性政治对非真相及其情绪性政治的有效抑制,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只是次要的和有限度的,其表现空间毕竟有限。但是,网络时代,民粹主义不再是次要的,而是直接走向前台,形成与三大主流政治相对峙并富于挑战性的第四大政治谱系。依拉克劳的分析,民粹主义本身成就了一种理性形式。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合流,本身就是吸纳民粹主义的结果。实际上,正是自1980 年代起,随着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的推行,西方兴起了新一波的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代表了一种来源于民粹主义者反对政治议程、制度化和混合式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合法性的当代民粹主义的形式。新民粹主义利用新的政治主张拒绝战后所达成的共同协议,同时努力建构一种新的作为自己的政党形式来表现其反对当前政治模式,特别是反对占主导地位的政党。”[3]新民粹主义不断被右翼政治力量所利用和提倡,正在产生令人不安的政治后果。2016 年来的诸多国际政治事件更是推动了这一态势,使得全球文明状况持续降低。与民粹主义相伴随的其他极端形式,如恐怖主义、暴政,等等,也呈愈演愈烈之势,令人忧虑。
依勒庞的判断,应对民粹主义不能诉诸于理性。“群体没有推进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4]在勒庞看来,掌握群体的本领或方式“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勒庞推荐的方法还是“通过杰出人物的意志”[5]。但是,我们认为,不能把民粹化看成是民众的本质特征,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的执政基础与理念,英雄主义被要求扬弃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过程。因此,不能把民粹化看成是民众的本质特征。
民粹化毕竟是一定的社会情绪的反映,积极应对之,是有益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无论如何,极端专制与独裁体制下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以及万马齐喑是可悲的,把那种灾难想象成后真相世界,必定是时代的错位与悲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毕竟只是封建专制时代的过时了的愚民作法。“民主”的本义即“多数人的政治”,与自由主义放任民粹主义因而总是被民粹主义所裹挟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多数人自觉意识到自身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不是成为无知的、非理性的大多数,甚至于沦为乌合之众。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然伴随着对民众的持续不断的教化与启蒙。启蒙的基本含义即开启明智,要让人民逐渐觉悟起来,融入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潮流,并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发展变革的主体。这的确是十分艰难的任务。毛泽东当年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邓小平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将是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于几十代人的历史任务,都已经估计到了对我们的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任务之艰巨。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矛盾交结,错综复杂,改革任务十分艰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正致力于通过关键少数团结带领大多数人奋力向前,落实治国理念,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尤其需要人民的民主政治意识跟上来,而不是为民粹主义所利用。
不能回避当下中国的后真相及其民粹化现象。当前的民粹化现象的实质(“真相”)正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延续下来的社会不公,相当数量的人群与社会主流脱域并边缘化,从而滋生了各种激愤的社会心态,这一状态很容易与改革开放前的“文革”意识(正是民粹主义)关联起来,加之网络时代巨大的表达空间,形成了当下时代的民粹化及其后真相现象。实际上,撇开网络时代真相的延迟效应,撇开对后真相现象的过分夸大或解读,后真相现象的实质就在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复杂难解,种种掩藏真相的话语,实际上是虚假意识形态。因此,克服民粹化,摆脱后真相现象对中国可能的消极影响,还需要正视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文明素养,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参考文献:
[1][4][5]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 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2、81、83.
[2]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11.
[3] 保罗·塔格特. 民粹主义.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00.
从后真相到新秩序:
别样共同性及其公共治理
陈忠
“后真相”似乎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概念与现象,但反思现实与历史,后真相其实并不神秘,有其踪迹、趋势与规律可循。厘清后真相的别样社会实在、社会情绪属性,分析后真相产生的语境、技术、体系等原因,把握“后真相”挑战既有体系、走向“后秩序”的内在机理,对于应对、规范、治理后真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后真相:复杂社会的别样共同性
这是一个日益复杂的时代。后真相是当代社会结构、社会共同体复杂化的一种构成、表现、特点。当代社会,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传媒化、传统化、区域化、本土化等趋势相互交织、相互纠结、相互嵌入。在这种复杂的交织中,人们的利益、情感、生存、发展等需要不断地具体化、多样化;旧的需要还未满足,新的需要已经产生;人们之间的生存、发展、利益、情感等关系不断地裂变、重组。在这个变迁加速、日益复杂的社会,每个人都成为一种叠加状态的复杂主体, 成为由日益多样的需要、能力、关系相互叠加的复杂人;每个人都同时性地归属于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又可能同时性地不归属于任何具体类型的共同体。虽然,进入社会、进入共同体是人类的历史宿命、终极命运,现代社会的综合建制日益完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社会建构已经完备、已经可以关照到所有的社会共同性,不意味着社会建构不再需要变化。现时代,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在稳定的背后,表现出深刻的流动性、易变性、叠加性、互嵌性。后真相反映与对应的正是当代复杂社会实在结构中的别样社会性,一种处于主流社会建构之外的别样共同性。
以日益发达、普及的传媒技术与日益便捷的交通条件为支撑,为了特定某种目的和需要,人们日益有条件如“闪客”一般即时性地快速进入、结成某种行动共同体,又快速地退出这个行动共同体。一方面,各类既有的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相互叠加;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也在不断生成。不管是后真相政治、后真相社会、后真相文化,或其他以“后真相”冠名的对象,其本质都是一种社会共同性,一种没有被现有体系和公共领域充分关注到的“别样共同性”“别样社会性”。后真相的深层本质是一种没有得到适当反映、认知、规范的共同主体需要、共同利益诉求、共同情感需要。任何对象特别是整体性对象都有其趋势、节奏、规律可循,以后真相命名的流动社会性、别样共同性也是如此。
其一,城市社会是后真相生成的综合场域。后真相是一种特定的空间与社会存在,是城市型社会的必然产物。反思社会史、文明史,任何历史阶段都会有其后真相,都会有不被主流体系、主流社会所把握、认同的社会共同性。但在城市社会语境下,主流之外的共同性、社会性具有了新的特点。一方面,城市化的推进过程是多样异质文明的聚集过程,也是多样社会性、多样共同性向相对有限空间中的聚集过程;另一方面,多样异质文明在聚集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要素、结构,新的主体需要,新的社会共同性。也就是说,城市化是聚集与变化的统一,在聚集与变化的叠加中,产生既有社会体系、社会建构、公共领域所没有反映、掌控、规范的另类社会性、别样共同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城市社会的推进,不断出现不同类型的后真相可能是一种常态。
其二,现代传媒是后真相生成的技术条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社会实在,后真相也是一种知识与情绪存在,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形成集体行动、具有社会后果的共同情绪、集体无意识。在传统的知识传播条件下,即使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体制之外的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利益情感诉求,这种体系之外的共同性也往往处于分散状态,很难形成集体行动,很难造成社会与政治后果。当代新媒体技术与工具的普及化,则深刻地改变了这种状态。以新媒体为中介与手段,原来处于分散、离散状态的潜在的别样共同性,有条件迅速成为具体的集体知识、集体情绪,并在特定条件下形成、催化某种集体行动、知识行动,对既有的社会建制、体系秩序、公共领域构成挑战。
其三,体系固化是后真相生成的制度原因。秩序是任何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而由不同、具体公共部门构成的公共领域则是实现与维护秩序的载体。但体系、建构、公共领域往往有天然的固化倾向。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科层制、专业分工、专业流程在公共领域中的推行,既提高了公共领域的运行效率,使公共领域成为维护社会整体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催生、强化了公共领域的独立化、保守化、固化倾向。在应然的意义上,社会建构、公共领域须是反映、规范、守护、发展社会多样需要、共同利益的重要设置。但实践运行面对变化的社会,面对不断产生的新需要、新情绪,公共领域、公共机构往往表现出具体的惰性、滞后性。体系、公共领域的固化,是导致新出现的社会共同性、社会诉求得不到及时反映、规范、引导、疏导,而成为一种对既有体系构成挑战甚至威胁的“后真相力量”的制度原因。
后秩序:对既有体系的别样挑战
后真相往往走向“后秩序”。后真相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在于后真相作为一种体系外的力量,对既有的秩序、体系构成了威胁与挑战,有可能使艰难建立起来的现有秩序进入一种失序、无序的“后秩序” 状态。对既有体系而言,问题的难度与关键在于,后真相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可能不再采取传统的方式。而是借助新的媒体工具,以某种集体无意识、知识隐性传播的方式,瓦解现有体系与秩序的知识合法性、信仰与信念的神圣性。在反思的意义上,在知识策略上,后真相力量自身,或假借、操纵、利用了后真相力量的某种力量,所直接瓦解与挑战的是现有体系的知识神圣性、知识合法性,通过质疑现有体系所建构的已有真相的真实性,通过还原所谓的真相背后的真相,通过追求所谓更为真实甚至细节真实的背后真相,让人们对现有体系所建构、尊重的知识、真相、道德、伦理、信仰、信念等产生质疑、怀疑。瓦解了一个体系的知识神圣性、知识合法性,也就在相当程度上瓦解一个体系的制度合法性、秩序合理性,瓦解了这样秩序本身。后真相对既有体系的挑战,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方式的别样挑战。其指向的是一种没有得到反思与确认的未来,其发泄的是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其导向的是对现有秩序的瓦解,而不是新秩序的建立。所以,与后真相对应的不是新秩序,而是“后秩序”——对现有秩序的简单破坏。之所以如此,其深层原因在于:后真相作为一种实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对隐性、分散的社会共同性,其本身就具有无序性、情绪性、离散性、非理性等特征。把握后真相自身的构成性特征,对于把握后真相对既有秩序的别样挑战,把握后真相的可能秩序走向,具有基础意义。
其一,后真相是合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后真相是当代城市社会、传媒社会所催生的一种别样共同体,反映、代表了仍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的新的利益与情感诉求,并指向对固化、僵化体系与既得利益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后真相是一种合理甚至积极的力量。但同时,后真相又是一种具有相当非理性特征的共同诉求,是一种处于自在状态,而不是自觉状态的共同性。也就是说,后真相作为一种力量,是一种没有明确的自我认知、自我知识、自我反思的相对离散性的力量。在合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中,特别是后真相天然的离散性、非理性,使后真相所代表的力量、群体、个体有可能无序行动,或被某种力量、组织所代表、象征甚至利用,成为某种力量借力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反思历史与现实都可以看到,后真相行动所导致的结果,有可能同后真相的真正群体的真正利益相偏离、背离甚至矛盾。
其二,后真相是利益性与情绪性的统一。后真相的深处是利益。虽然利益不是后真相的全部,但利益性却是后真相的必然属性。表面看来,作为一种策略,后真相所追求的是一种所谓的真正的真相,后真相似乎并不追求或代表什么利益,但在所谓追求真相的背后总有利益的影子。没有同利益无关的真相,也没有同利益无关的后真相。当人们挑战某种真相时, 其真正挑战的往往是代表、建构这种真相的主体的利益;当人们追求某种真相时,其真正追求的也往往是这种真相背后的或象征的利益。后真相所挑战的不仅是既有的知识生产方式,不仅是既有的权力生成与运行方式,更是既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但也应该看到,后真相的这种利益追求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程度,还没有凝成成熟的共同情感,还处于相对情绪化的阶段。可以看到,后真相行动往往具有一定的甚至强烈的情绪发泄色彩,这个行动并不希望追求真正的真相,而往往只是以追求所谓真相的名义“污化”“归罪”现存体系,其所采用的手段也往往并不道德,甚至不把道德性、真实性作为自身的原则和标准。
其三,后真相是生成性与土壤性的统一。在每个时期,都可能生成后真相情绪,都有生成后真相的条件与土壤,但后真相成为一种普遍甚至蔓延的社会现实,则只可能生成于变化加速、时空压缩的当代社会。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还未来得及熟悉与把握一种新对象、新现象、新信息,又产生了更新的对象、现象、信息,这种快速的变化给人留下没有真相、来不及追求真相、追求真相没有价值的印象和感觉。也就是说,社会变化与信息变化的速率过快,是后真相情绪生成的重要土壤。同时,当后真相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与社会情绪时,又成为催生当代社会产生更多变化、更多信息、更多不确定性的土壤。作为这个社会的不确定性之生成物的后真相,又成为使这个社会产生更多不确定的土壤。一方面,生成物在土壤中生成;另一方面,生成物本身又成为了土壤。在这种相互生成、相互反哺、互为土壤中,人与群体的各类合理与不合理需要都可能不断生成、膨胀甚至裂变。由此,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甚至可能成为一种从未有过的“传媒型风险社会”“情绪型风险社会”,一种“后秩序”社会。
新秩序:营建开放包容公共领域
在土壤性与生成性、利益性与情绪性、合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中,后真相是利与弊的统一。一方面,后真相作为一种另类的知识和另类的情绪,反映了当下社会存在的某些重大问题、结构性问题,并促使人们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后真相毕竟是一种非建设性、情绪化的社会存在,会对社会的整体秩序产生作用方式与发展方向都具有不确定性的威胁。当代社会已然是一个实然性的后真相时代。在后真相时代,社会在总体上有可能加速向好,也有可能加速向坏。关键在于如何应对,能否合理应对、治理。
其一,营建更具弹性、共享、规范的发展格局。后真相问题之所以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既得利益、发展机会的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当主流社会建制不能反映、规范、满足新产生的社会利益诉求时,就会产生游离于主流社会建制之外的社会共同性、社会群体甚至集体行动。后真相正是这种体系外的社会共同性的一种形式与表现。建构更为开放、平等的机会与财富共享机制,克服利益固化,为更多的人提供发展机会,使更多人共享发展的机会与发展成果,对应对后真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营建更具确定性、民族性的文化与信仰格局。作为一种特定的情绪、知识、意识形态,后真相问题之所以产生,之所以成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公共领域、主流社会相对忽视了营建更具确定性的文化与信仰格局;或没有找到适合现时代特征的文化与信仰营建方式,没有找到自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方式,从而使各类非主流的意识、信仰相对随意生长、无序发展。营建传统与现代相统一,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更具有包容性、确定性的意识形态与信仰体系,是应对后真相问题的重要知识行动路径。
其三,营建更为开放、包容、规范的全媒体环境。当代新媒体是催生后真相问题的重要基础,正是以各类新媒体为介质,后真相成为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和后果的知识实在。反思文明史,每一次知识传播方式、传媒技术的变革,都伴随、催生新的社会甚至政治变革。如何评估、预判、适应、规范当代新媒体技术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后果,具体用什么方式推进与规范新媒体的发展,人们有不同的意见。发展与规范、自由与责任相统一,是治理新媒体的重要原则。营建开放与规范相统一的全媒体环境,对于减少后真相的减效应,引导其向有利于社会整体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四,营建更为开放、包容、规范的公共领域。虽然,现代社会的各类正式与非正式公共领域,比如政府部门、工会组织、各类社会组织等似乎已经发育、建构得比较完备,但相对于当下快速推进的城市社会、媒体社会而言,目前的公共领域、公共部门的构成方式与运行方式都表现出一定的问题,并不能及时反映、掌握社会已然产生的变化。当公共领域不能反映、代表社会需要,社会就会生产游离于体系之外的公共性,并可能对现有公共领域的公信力、合法性产生质疑和挑战。公共领域的固化、僵化,公共领域对社会变迁的反应速度过慢、反应能力不足,是导致后真相向失范、无序方向发展的重要体制性原因。改善政府部门、工会、社会组织等各类公共领域的运行方式,建构更为开放、规范的公共领域,对于应对、规范后真相时代具有制度意义。
总之,作为一种实存,也作为一种概念,后真相社会是对历史终结论、社会终结论的深层别样挑战,也是对既有秩序方式、既有知识生产方式、既有政治合法性、既有利益结构等的新型别样挑战,是社会变迁特别是现代性之不确定性、复杂性的又一次呈现。但以“后真相”命名的不确定性其实并不神秘, 其本质是一种处于特定的潜在状态,被主流建制所忽视、漠视的社会实在、社会共同性,是一种不同于既有社会共同性的“别样的共同体”。以当代新媒体为介质,这种“别样的共同性”有可能或正在生成为一种“别样的公共性”。针对特定的问题,这种别样共同性会生成一种别样的集体行动,一种另类的集体知识行动,并产生特定甚至巨大的社会后果、政治后果。面对这种后果,受限、依附于既有知识、政治、利益体系的人们,把这种问题与价值兼有、实实在在存在的“别样公共性”有些否定甚至歧视性地归类为、称之为“后真相”。但这种所谓的后真相并不是假象,而是一种另类、别样的真相,一种新型的社会共同性、社会公共性、共同知识与利益诉求,也是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力量。后真相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问题性。以漠视、排斥、压制、简单否定的方式应对后真相,效果不会理想。建构更为开放、包容的新秩序,推动社会建制构成方式与运行方式的进一步合理化,对于应对后真相问题、规范后真相力量,具有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