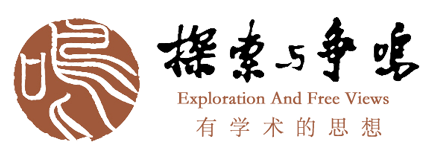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琐事与真理
——对王建疆“主义的缺位”命题的进一步讨论①
阿列西.艾尔雅维茨
内容摘要 某个国家和地区在特定的时间内其艺术和人文学科之间会有发展并不一致的现象,这似乎在说明真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之间的矛盾。中国当代在世界上具有引领作用的艺术往往都是“出口产品”,与本国的观众无关,而且本国的学者也对此所知甚少。王建疆教授的“别现代”理论在批判思想欠发达现状的同时,呼吁中国的美学也要领先世界;但在我看来这一主张有些夸张,也未必如此,因为中国美学缺少中国当代艺术那样的内因和影响力。中国美学的出路在于瓦解“同一”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关系。
关键词 琐事 真理 中国当代艺术 中国人文学科 领先世界 别现代
作 者 阿列西.艾尔雅维茨,斯洛文尼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译 者 徐薇,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文艺学博士生、南通职业大学讲师。
当提及知识等各个领域的总体情况时,我们常常假设不仅我们的起点而且对话者的起点也是一般相等的抽象(因此是空洞而且不确定的)范畴,也就是说,我们假设在某一文化或者语言环境中,不同的领域已经发展到一个相似的阶段。因此,比如说,我们一方面涉及中国文化、人文学科或者美学在中国范围内影响的程度和水平,另一方面参考它们在全球背景下的影响,并且假设在两种情况下,这些活动已经发展到了近乎相同的程度。但是真的如此吗?
真理是抽象的还是琐细的?
真理一般都被认为是具有抽象意义的,也就是普遍性的。但是在面对当代艺术,也就是被归属为不同国别的艺术的时候,所谓的真理又显得非常具体,甚至琐细。就如王建疆教授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参与讨论的“主义”一样,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和事实上的差异。这是因为,在西方,“主义”一词更多地体现为观念、方法和流派的运动,这与中国的主义除了这些功能外还有将主义神圣化的倾向根本不同。至于说到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包括中国当代艺术,要从其中找到一个抽象、普遍的真理似乎很难。我经常有这样的体会,作为艺术理论家、批评家或者实践艺术家的中国同仁们,把中国当代艺术或者当今的中国艺术笼而统之地看作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时尚潮流,远离西方艺术对他们来说似乎更加稳定,更像是古老而又持续的传统的一部分。即使他们正在考虑当代艺术,但他们认为当代艺术似乎常常拥有非常短暂的生命。换句话说,在我看来,中国艺术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与西方艺术在西方国家的地位非常相似,然而中国的学者们却不这样认为。因此巨大的差异是——或者直到最近一直是——艺术在每个不同地域的接受:在西方,这种艺术被认为真正地具有当代性和“国家性”,即使处于全球化的同一时空,但与此不同,直到最近,中国的艺术都是出口的艺术(exportart),这是因为,尽管它在外国吸引了很大的关注,而在中国产生的反响是相当贫弱的,甚至不为学者所知。对此,我批评过中国美学家对当代艺术的无知。[1]显然,这里有着中国学者对中国当代艺术,尤其是出口艺术的隔膜。这种隔膜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是出口艺术呢?我想,中国的学者应该比我有更清楚了解个中原因。
几年前两位法国艺术评论家丹尼尔?格拉内(Danièle Granet)和凯瑟琳.拉穆尔(Catherine Lamour)根据国家和经济的趋势、期望等等,研究了艺术市场的现状、艺术的风尚、艺术的影响、利润、推广和全球定位。这项研究以“艺术世界的大秘密和小秘密”为题,最初于2010年在法国出版。[2]两位作者认同中国当代艺术是当代世界艺术中杰出的范例之一,无论我们以哪种标准判断或者评价它。我由衷地同意这样一个评定。
2007年,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市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有关中国当今和当代艺术的书籍——大多在海外如美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且常常以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出版。大量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专著也在此后出版,但是这些专著、展览和艺术市场的存在基本上还是为了使外国公众受益。与萌生了后现代的后社会主义先锋艺术的其他国家相反,在中国这种当代艺术是出口艺术的领域,它对中国当地的艺术家和当地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领域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所有这些显示了我的中国同事们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常常是不确切的:中国艺术不只在欧洲、东南亚和美国受重视,就是在中国它也是有价值的,但是许多人对它的认识的起点,还没有到达一个它应有的“正常”的位置。目前,它仍被困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的不同且对立的各个领域之中。
与王建疆教授之间的这场讨论,是从他提出的主义以及别现代主义开始的。[3]他的别现代并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而是似是而非的需要区别的现代。[4]这样一来,我们之间讨论的主义问题就又遇到了真理的普遍与特殊的难题。思考这一难题,我发现对于真理认识的地域性和主观自信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东亚也普遍存在着。
在以前的一届国际美学大会上——2010年北京举行的那届——一群日本参会者为了让其他与会者受益特别展示了茶道。因此一群日本女士在每个大会日的早晨到达大会的现场,准备茶、用具等,直到晚上都在耐心地等待碰巧经过的路人进入正在不定期地举行茶道的房间,然后体验这个仪式。尽管日本参会者为使其他与会者进入茶室做出了明显的努力,但许多人选择不去体验茶道,这让我感觉也许这个仪式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在我看来,他们不去的原因可能在于代表们忙于大会的议程,因此无法从他们宝贵的时间中分身参加诸如茶道之类的活动。在一次与日本同行讨论茶道仪式所引发的冷淡的反应时,他们的回答是,“不,不,茶道取得了圆满成功,对那些想要了解它的与会者来说,目的已经达成了。”虽然对于这个观点我有些惊讶,但还是勉强同意了我的日本同行的意见,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的说辞还确实有几分道理。
无独有偶,2000年我参加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之后,与会的一些朋友和两位韩国博士生一同走访韩国各地,在途中游览了风景如画的雪岳山(Seoraksan National Park)国立公园。到达雪岳山后,我们登上了缆车前往其中一座山巅。就在乘坐缆车的过程中,车厢里响起了音乐的旋律;令人惊奇的是,我们觉察到这是奥地利的“波尔卡”音乐,一种来自欧洲阿尔卑斯山的民间音乐,主要在奥地利、巴伐利亚(德国东南部)和斯洛文尼亚流行。这些歌曲都是极其地道(authentic)的,而且也用德语演唱。在韩国中部听到来自阿尔卑斯山的民间音乐,我们都非常诧异,于是询问其中一位韩国学生为什么这里会选择这样一种音乐。他回答说:“嗯,这是真正的(authentic)韩国音乐!因为我们在山里,所以就放这样的音乐。”最后一句话很有道理——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样一个事实上来:阿尔卑斯山就像韩国群山的兄长——前一句却听起来有些空洞。尽管如此,我们知道“真实性”(authenticity)的概念在这里以一种不同于它通常意义的方式被使用。
就像日本茶道的案例一样,这一次我也在寻找一种路径,来解读那些给予我们外国人的回答,它们以一种完全严肃的方式呈现给我们。
王建疆教授的主义,包括他自己的别现代主义,似乎也有这种东亚的地域性和自信心,但是,他所讲的主义更多的是要跻身世界舞台,展现大国学术地位的主义,也就是对普遍真理的共享。为此,我曾撰文认为,中国学者对于主义问题的讨论会使中国成为世界哲学四边形之一边(“哲学四边形”是我提出的概念),从而改变目前的世界哲学格局,但是,从发出声音到取得发言权仍然具有很大的距离。一方面是自信和坚持,另一方面还需得到普遍认同。[5]
当代中国美学没有必要领先世界
前述格拉内和拉穆尔所写的那本书——特别是它的第八章——告诉我们什么?它为我们提供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许多不同的事件、人物和发展,在这方面给出了总体的概述,如同90年代全球有影响力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比如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和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提出的那样。两位法国艺术评论家(格拉内和拉穆尔)也已经在上述的书里揭示了一个大约一百人的网络,他们引导且控制了全球艺术世界的形势。他们不一定是艺术品收藏家中最富有的,也不是从艺术品买卖中获利最多的人——但他们离这个目标已越来越近。今天中国艺术家在各种当代艺术形式中都有强烈的表现:王广义等人的作品与那些来自其他地方最昂贵的作品被同样地展示和购买,而且价格上也可与它们相媲美。不仅买进卖出,而且还频频展出,受到重视。有趣的是,来自中国的艺术品仍然带有一种使命,一种存在的理由,使得它们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当代艺术。
它们和这个艺术界所涉及的艺术,与20世纪各种运动以及它们的理论或者哲学的支持者们已经发现的他们时代的真正的艺术恰恰相反。我们的当代艺术(加上所提到的中国的例外),似乎不再具有一种颠覆的、批判的或者存在主义的功能或者潜力。艺术是一种稀缺的商品,更多地取决于它的稀有性和推销性投资,而非在任何具体的社会群体中所起的任何特殊的作用。相关的艺术包括杰夫.昆斯(Jeff Koons)、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和村上隆(Kurakami)的作品。在这个方面,由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和类似的艺术评论家所推动的艺术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和人的价值;在“最著名的”、“最受欢迎的”艺术品的例子中,什么艺术将被展示、讨论和买卖几乎完全由市场以及那些控制了独有的象征性资源和金融资源的人所决定。
中国当代艺术如何适应这样的场景?自从哈罗德.泽曼(Harald Szeemann)1980年策划了第一个“威尼斯双年展”的开放展之后,中国艺术一直是世界上最有推进力的国家艺术潮流之一。在它的第一个阶段——1980年代(或者换一种说法,在“文革”和它的余波之后)——中国艺术仍在找寻它自己的“身份”。那个时候,最知名的作品都以极具煽动性的方式命名,但尽管如此,仍在与当时俄罗斯“改革的艺术”传统意义上相对等的艺术的边界之内:它们有了这样的名字,比如“玩世现实主义”。与来自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确立的和同化的艺术非常一致——即我们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社会主义条件:后期社会主义之下的政治化艺术》中已经呈现和探讨的艺术。[6]以这种方式,中国当代艺术是最后加入我所说的“后社会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或者“第三代先锋”的世界艺术潮流之一。正如它东欧和古巴的兄弟,它踏上了世界舞台,展示了它的特点——随着全球社会的变化——已消失在一瞬间。然而,在它的背后,在每一个国家之中都留下了一些尚未拆除、没有被同化,没有挂另一个品牌销售的残留物和一些特征——即使它们都是这样,它们也暴露了这种历史的特殊性,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它仍然引人注目。
所有这些都证明,至少在视觉艺术中,中国艺术不仅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处于同等地位,而且甚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它变成了一个全球当代艺术中各种潮流的非官方的领导者。然而,尽管如此,当代中国艺术在中国的地位却被边缘化了。但与中国当代艺术在国内的际遇不同,这种中国当代艺术,即出口艺术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获益,恰恰显示出中国学者在人文学科和美学领域过去和现在所追求的目标。人文学科和艺术的结合,虽然每天都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在中国的艺术批评和美学中却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这两个领域(人文和艺术)在认识论上相距甚远,它们很难从一个包含了艺术和理论的共同特性的立场考量,二者可能此刻在本质上仍是分离的,尽管它们都还是早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囚徒。
在经过一场漫长的斗争后的今天,中国当代的视觉艺术已经被无缝地整合到“全球当代视觉艺术”中,此外,它作为一个例子,也许已经是全球范围内的领导者的作用。然而同样的艺术直到现在,才在中国被赋予了“公民”的身份。但是迄今为止,这还未发生在中国的人文学科之中,因此,王建疆教授有足够的理由去批判中国人文学科的现状②。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只有在内因大于外因的时候才能够建立(和增强),也就是说,中国当代人文学科必须感受到有与中国当代艺术融合并且参考中国当代艺术的必要性。当这一切发生时,中国的人文学科和美学将发现它们拥有一个强大的有天赋的盟友,这个盟友被艺术家们忽视或者低估,但是现在正在显示出一种未被人察觉的支持的力量。在某些方面,中国与中国艺术的现状很像阿瑟?丹托描述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情况:艺术远未消亡,它只是发现了理论,以及这种理论可以为其他地方的艺术实践提供的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支持。
这一切都证明尽管中国今日人文学科的现状如此,但中国的美术和视觉艺术一般而言是极其发达的,甚至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世界上任何文化和国家都乐于在全球艺术世界中拥有这样的地位、影响和存在。但在王建疆教授看来,这显然并没有那么重要。他认为,似乎人文学科和美学(在世界上)也必须与西方理论在中国或者中国理论在中国一样发达和有影响力。我认为这是两个夸张:不是所有人类的创造性和活动的领域能够或者必须达到同样发达的程度。对于中国当代美学而言,没有必要跻身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美学之一(虽然这很好),正如对日本茶道来说,没有必要成为与西方喝咖啡“礼仪”相等同的仪式。
这些都是琐碎的真相,但它们同时又是普遍的真理。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中国美学将发展到与西方美学相同的程度”的表述是否有意义——特别是——表达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实际需要吗?我的回应是:没有。原因就在于除了前述中国美学与艺术的脱节外,还有一点就是缺乏影响。我们可以重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话:如果你想知道一个词的意思,看看它是如何使用的。更重要的是,看看它是如何被频繁和广泛地使用的。如果缺乏这两个条件,即使中国美学如何强调区域性特色或者琐碎的真理和十二分的自信,也都不可能引领世界。艺术品的国际影响在于世界市场的认同,而美学的国际影响却需要美学对于普遍真理的发现及其这种发现被使用的频率和范围。
如何瓦解“同一”与“他者”之间的对立
现在让我来揭示一下这篇文章主题的出发点:正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名著,法文题目Lesmots et le schoses(“词与物”),译成英文版后改成了《事物的秩序》。在这本书里,作者分析描述了知识的形构。在这个方面,福柯的这本书与我在本篇文章里提到的主题和问题非常接近:日本茶道不就是并非取决于参观者的人数而依赖仪式的出色的过程来判断成功的一种有组织的活动的案例吗?韩国雪岳山国立公园里播放阿尔卑斯山民间音乐不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可能被强制性地与奥地利(德国)的阿尔卑斯山而非与韩国的山岳相关联,它们在全球范围来看没有代表任何特殊的一座山,因而它们可以根据自身与世界上最著名的山脉——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斯洛文尼亚的阿尔卑斯山的相似性或者联系来欣赏吗?
《事物的秩序》第一段的开头这样写道:“博尔赫斯作品的一个段落,是本书的诞生地,本书诞生于阅读这个段落时发出的笑声,正是这种笑声动摇了我的思想(亦是我们的思想)所熟悉的东西,这种思想具有我们的时代和地理的特征。这种笑声打破了我们习惯于用来控制各种现存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的平面,并且在以后很长时间持续地扰乱并带来瓦解我们关于‘同一’与‘他者’的古老的区分的威胁。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其中写道,‘动物可以分为:一、属皇帝所有的;二、有芬芳香味的;三、驯顺的;四、乳猪;五、鳗螈(美人鱼);六、传说中的;七、自由行走的狗;八、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九、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十、不可胜数的;十一、用非常精细的驼毛笔画出来的;十二、其他动物;十三、刚刚打破水罐的;十四、远看像苍蝇的。’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通过寓言向我们表明另一种思想具有的异乎寻常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的限度,即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思考。”③
福柯这里所呈现的来自早期后现代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作品的片段,是一种理性的巧妙——“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个片段典型地表现了中国——西方这一对概念的倒影。在博尔赫斯和福柯的时代,中国仍然代表遥远的和异域的——是无法理解的他者,却从那以后变得更加为人熟知,但是在其中——如中国当代绘画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陌生的岛屿,不可理解性和他者性仍然存在,只是今天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加相信这一点。
我来把这篇文章总结一下。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公众将继续吸收中国当代绘画,尽管它离中国传统艺术相当遥远。绘画就像说一门外语:首先我们欣赏它却不理解它;之后我们理解它,但它听起来在其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却是陌生和难以理解的。接下来,它被模仿和翻译,最终被同化和转换为更广泛的(和转化的)文化的一部分。最后我们不再注意到它的陌生和差异了;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个,不再是“他们”的了。有时,他们中的一个原来是我们中的一员。不管怎样;我们把艺术看作是两者——众多流动的日常语言和思想中的两个——之间的桥梁。中国的人文学科如果不安于现状,也会取得成功。我认为王建疆教授的努力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因为他通过他的别现代主义展示了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因。但中国美学要像中国当代艺术那样领先世界,还需要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看看它是如何被频繁和广泛地使用的,也需要如福柯所说的如何瓦解我们关于“同一”与“他者”的古老的区分。同一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有关真理的抽象与琐细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文学科包括美学能否取得与中国当代艺术相近的国际地位的问题。
注释:
①本文最早译自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琐事与真理:对王建疆有关“主义的缺位”命题的进一步讨论》(见《全球视野中的别现代艺术和人文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7月,上海),此次公开发表时艾尔雅维茨又做了个别修改。根据阿列西?艾尔雅维茨本人的建议,有关王建疆观点的几个出处除了英文文献外,从王建疆新著《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进行了相关引述。——译者
②Wang Jian jiang. The Bustle and the Absence of Zhu yi.The Example of Chinese Aesthetics.Filozofskivestnik,2016,37(1);王建疆:《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8-61页。
③本段译文参考刘宗迪:《怪物志、本草修辞学以及福柯的笑声》,《古典的草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参考文献:
[1]阿列西.艾尔雅维茨.主义:从缺位到喧嚣?——与王建疆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16(9).
[2] Danièle Granet、Catherine Lamour. Big and small secrets of the world of art.Paris: Fayard, 2010.
[3] Wang Jianjiang. The Bustle and the Absence of Zhuyi. The Example of Chinese Aesthetics. Filozofski vestnik, 2016,37(1);Wang Jianjiang.Quadrilateral in Philosophy, Aesthetics and Humanities and Bie- mod- ernism.Art & Media Studies, 2017(13).
[4] 王建疆 . 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 . 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5] Ale Erjavec.Zhuyi: From Absence to Bustle? Some Comments to Jianjiang Wang’s Article“The Bustle or the Absence of Zhuyi. Art & Media Studies,2017(13).
[6] Ale Erjavec.Postmodernism and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Politicized Art Under Late Social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