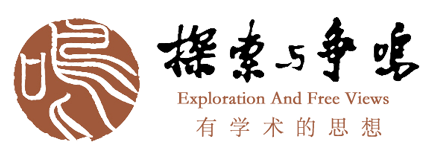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悲欣交集:“失败”青椒的私人编年史
编者按 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后,大量的年轻学人作为新鲜血液被补充到大学教师队伍,他们被戏称为“青椒”。“青椒”群体学历光鲜,产出惊人,对所在高校的学术成绩贡献十分可观。他们是莘莘学子的职业梦想,是学术世界的明日之星。然而,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他们为何选择学术道路?有何学术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生存现状如何?如何看待和实践自己的学术发展之路?
关注中国未来学术发展,关注“青椒”群体,《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推出“青教心声”专栏。本专栏推出后取得了一定关注,一些高校青年教师纷纷来稿,他们分别从自身视角,于字里行间展现当代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状态。从本期起,本专栏将陆续刊发专稿,透过诸多个体的亲身经历,多方位展示“青椒”或辛酸或坚韧的心路历程,诉说这一群体的心声,力求为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的进步,提供第一手资料。
2012年:没有世界末日,只有小确幸
有时想想,自己已经够幸运了。刚刚读研那会,从未想过自己也有可能成为一名大学老师。也感谢一路上诸位师长的栽培与错爱,让我于2012年的那个夏天在这座湿热的南方小岛上落脚。现在再翻看那时写下的字句,心境果然大不相同。在一篇投给《南方周末》“落脚城市”栏目的短文中(当然未被采用),我的踌躇满志跃然纸上:“眨眼九年过去,我像来回穿梭的太阳射线一样,带着理想与信念,由南向北,再由北返南。如一叶浮萍,从四川的大山走出,翻越秦岭,客居京华,又携梦归于福建的大海。又似一粒麦种,由学生变为教师,由稚子升作人夫,从一个学校走向另一学校,并最终生根发芽在这校园。”
这校园据说是中国最美的大学之一。当年耽溺于校园民谣、曾在情书上誊过《冬季校园》的我,而今竟能任教于这首歌曲的诞生地,果真有那歌中的“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也不知能否遇见“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只是,这里的夏天如此漫长,让人忽略了四季的流转,不知这真正的冬季校园,又是否会如我当年所听与所想一般?备课,讲课,出题,改卷,担任本科生导师,与大一新生一同成长。偶尔能蹦出一两句金句,但更多的是紧张与青涩,最怕在课堂上突然卡壳。幸有身边的师长提点两句,才慢慢逐渐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
那年的冬天,初上讲台的我,没有了北方暖气的庇护,并没有感到有多冷,但也在匆匆之中忘了用脚步去丈量下这校园。好在,妻子背后默默支持,留饭留灯留洗脚水,家人在远方也平安无事,日子过的简单而又平凡。
2013年:万事不止开头难
一年过去,2013年的我没有变秃,更没有变强,只是感觉自己的肚子在慢慢变大。当然,多的不是墨水,而是脂肪。或许是生性散漫,离开了师父的督促,自己渐渐有点放飞自我,按部就班上课下课,科研事业确没有什么起色,就连最不费力的博士论文修改工作也一拖再拖。又兴许是眼高手低,陆陆续续投出去的论文无一例外被退稿,试着写了几个课题申请书也差不多石沉大海。打开电脑看着审稿系统页面上那神秘的几个***,开始隐隐约约感到一丝压力,原来大学老师也并不轻松啊。
在一次参加“青椒会”(我们学院还真的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的时候,我趁着酒兴开玩笑说了一句,“可能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学术G点”。同事哄笑之余也不忘实力补刀,“说不定你就是个性冷淡”。而另一位同事W,也因为转投当时并不热门也并不被看好的神经元法学(法律认知科学?),得一绰号,名曰“神父”(神经元法学之父?)。
2014年:继续“丧”下去
到了2014年。一方面,课讲得比以前好多了,PPT的制作技能也比以前有所提高。要知道,来这校园试讲之前,我才头一次知道,原来PPT是可以动的。当然,现在想来,我把过多的热情投入到了教学中去,以至于当时学科带头人主动与我搭档授课时,我被《职务聘任条例》上的那句“完整讲授一门本科课程”所带偏,婉拒了领导的这份好意,而且还被要求(因学制学分问题导致该届学生无课可选)硬着头皮开过一门研究生新课。而啃下这门课后再也没有上过,那些熬夜备课早起上课的个中甘苦自然也无处可以诉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课就已经讲得有多好了,唯一的收获是参加了校青年教师技能大赛,进入决赛后勉勉强强拿到一个校二等奖。
另一方面,论文发表还是颗粒无收。也很难说自己没有动笔,但没有勤动笔这点是抵赖不掉的。就像博士毕业前夕,师父曾经苦口婆心对我说的那样,老师们都比你们拼。一天课下来,口干舌燥,昏昏欲睡,于是就开始嫌累了,不想熬夜了,也没有几个时候是能够做到心无旁骛的沉浸式阅读与写作。同时,想要复制以前“打擦边球”的发表经验(读博期间有幸在宗教学头号刊物发过一篇),拉拉杂杂读些其他学科的论文就想去分一杯羹,现实分分钟告诉我,原来我的经验不像唐骏的一样可以复制。零星发表了一些在评价体系中没有用处的论文聊以自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除了焦急,也只能焦急。
现在回想,除了自己感觉科研还没有上手之外,我对于家庭与工作的兼顾确实也不尽人意。比如,房子刚刚装修完后就迫不及待接母亲前来与我们同住。孝心固然可嘉,陪伴固然重要,但也忘了有时候这并不意味着皆大欢喜。此地湿热重,母亲并不喜欢,加上人生地不熟,我与妻子又天天早出晚归,实际上母亲也大多独自一人在家为我们买菜做饭而已。各种生活习惯的差异也慢慢埋下了婆媳关系的“雷”。而我这个夹在中间的笨拙士兵,既不能探雷,也不能排雷,只能在日记本里倒倒苦水,殊不知这雷迟早有一天是要炸的。
而就在自己继续“丧”下去的同时,身边陆续有年轻同事开始跳槽转会。尤其是隔壁办公室的两位青年才俊更是同时光荣返京,跻身京城学者行列。一时间坊间对于这间办公室的风水颇有好评,据说之前的前辈在此没呆多久便被顶级刊物加持,一下子到了P大,让人好生羡慕。铁打的高校,流水的青椒,前前后后,进进出出,同时期的好像就剩下我一个了。
2015年:涉险过关
2015年年初,开始做噩梦,梦见人事处打电话来问,这三年你都干了什么。在惊出一身冷汗的梦醒时分,格外清醒。但听过那么多的道理,仍然发不出一篇论文。盘算这三月一轮的投稿周期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方才醒悟过来这样下去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厚着脸皮给师父写了邮件请他指点迷津,师父第一时间专门回电问我:“你现在怎么混成了这个样子?”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这让我十分汗颜与倍感愧疚,恨不得有个地缝立马钻进去。好在之后,峰回路转,涉险过关,蒙某C刊厚爱,论文得以如期见刊,而那位至今素未谋面的编辑让我至今感念在心。无以回报,就如她所说一样,期待有更多佳作。
当然,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只有自己知道,这一危机也对自己的浑浑噩噩与碌碌无为敲响了警钟。首个聘期就把自己搞的如此被动和狼狈,这以后的职业生涯可又该如何发展?聘期考核尚且如此,遑论想都不敢想的职务晋升?
填完一大堆数据,签完考核表上的字,我才敢稍稍舒一口气。回到家中,等我吃饭的是身怀六甲的妻子,不想让她过于担心。两个月后,可爱的女儿诞生。
2016年:命运总是那个最善于偷袭的对手
女儿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初为父母的喜悦,同时也意味着肩上的责任更加沉甸。女儿一天天长大,我们也不再是手忙脚乱的新手父母,每天下班最开心的事就是回来抱抱她。也得益于相对自由的大学老师工作时间,我这个粉红奶爸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与她相伴。有一次扎在带娃的老人妇女之间,旁人艳羡地问我是不是某大学的老师,在得到肯定答复后自言自语难怪还有时间带娃。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无法替妻子分担太多,午间妻子驾车往返跨海大桥替娃做饭,除此之外,夜奶哄睡等事还得妻子亲力亲为。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劳累,2016年的一个黑色周五妻子终于倒下了。
说来也怪,平日都不在办公室加班的我那天鬼使神差地选择了加班,想趁机把课题的事情好好捋一捋。8点左右,家中来电,妻子洗澡后人事不省。不在第一现场的我,急急忙忙打车赶回,急电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关于此事的整个过程到现在,我仍然不愿轻易提起,当时所用的手机也被我弃用。太多眼泪,太多悲伤,不忍看,也不愿回忆,但所幸总算保住了妻子的命。这场大病(隐源性脑梗死)让妻子年纪轻轻就要遭受如此大难,与死神擦肩而过。这场变故也差点让我丧偶,让我们的女儿差点失去了母亲。而这一年我们刚刚三十出头,女儿刚刚长牙,生活才刚刚开始走上正轨。
原以为之前的各种不顺就已经是谷底了,算命先生也说过女儿一岁后我会上运。2016年我刚刚拿下梦寐以求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这对每个“青椒”来说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只是这样的喜悦之感在我这里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命运总是选择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对我们进行暴击,而立之年,我们却被打得立不起来,只能跪地求饶,哪还顾得上什么别的。
引用朴树的一段歌词:
“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
只想永远的离开/
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
想挣扎无法自拔”
再改写他的一句歌词,“还没有开始牛*过,就已经颓了。”
2017年:好在能陪她一起康复
妻子突患重病,我完全没想到,平素她的身体素质比我要好。此病凶险至极,非死即残。资料显示,小于35岁青年人发生的脑中风占全部脑中风的9.77%,以缺血性中风为主,男性居多。而妻子偏偏就是这9.77%。通过一年多的治疗康复,最苦最困难的时候好歹已经过去,家人的无私付出也是我最坚强的后盾。妻子插过鼻管,坐过轮椅,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遭的罪受的苦我不敢细数。2017年10月,我向某知名育儿公众号上投稿自述此间心路历程。本是一次不该公开展示的心理救赎,但未曾想到推送之后竟然引起了极大的情感反响。久未见面的高中同学在育儿群看到后默默给我发来加油的信息,学界师友看到同事转发后纷纷转致慰问之意,甚至连素不相识的微信读者朋友还打赏表示心意。
妻子单位的领导看到后也专程致电,表示让我们不用有太多后顾之忧,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尽力康复。我指导的研究生们也很明理懂事,其中一位女同学选定导师后与我正式见面竟然是在医院,而另一位原籍本地的男同学不辞辛劳坐车坐船带着家人攒了很久的土鸡蛋前来看望。所以,每当我写下这些感谢的句子时,内心总是自然而然充满对他(她)们的感激。当然,在妻子住院期间,更要感谢我的领导、同事为我尽可能地分担了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没有他(她)们的鼎力支持我不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照护妻子。也拜相对灵活的工作性质所赐,我在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之余,能够有相当的时间陪她一起坚持康复。这在其它工作中近乎侈谈,要么辞职走人,要么雇人护理。
2018年:我有两个女儿
现在妻子总体状态恢复不错,身体机能基本康复,唯独因双眼动眼神经麻痹而留有眼睑不能上抬等中风后遗症,同时伴有因眼位不正而导致的复视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可解的,有的可能在当下是无解的,但没准未来哪一天就可能有解了。每当说到这个的时候,我总自责自己不是医学博士,没有办法在专业上帮到什么。作为一个法学博士,好像能陪她做的就是说说话,打打球,散散步。所以,如果您在这校园里看到一位眼睑粘着胶布的女性,有时与一名男子同行,有时拉着一名女童,有时三人出现在一起,请您不要太介意她以这样的一副形象出现在您面前。她本来不是如此,也不愿如此,至少在我心中,她一直都是与我最初见面时的模样。
患病之后,妻子常说对不起我,常常突然就流下泪来,常常觉得给我添了很大的负担,拖了我的后腿。冷不丁还会问问我,论文最近有写吗?饭碗还保得住吗?你要不再娶一个吧?我带着女儿回老家吧。
我也常常跟她开玩笑说,我现在有两个女儿,你是我的大女儿,不过大女儿有大女儿的好啊,不像小女儿那样,有时吵着吃零食,有时要看《小猪佩奇》,有时还不愿意好好睡觉。说完这话我心头往往一酸,或许正是以前没把你照顾好,才让你变成了大女儿,现在整个人要换一个活法。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好了很多,或许我们应该知足。
比如,当我下课时间太晚无法去幼儿园托班接女儿时,是她踉踉跄跄步行大半个学校穿过马路去接孩子。在细雨中,在骄阳里,也是如此,生怕去晚了女儿看到小伙伴纷纷被接走时会有小失落。再比如,晚上我能偶尔能坐在办公室里,打开电脑修改那前途未卜的论文,而妻子看着女儿在学院旁的篮球场上与同班同学嬉戏打闹。我们不知道球场的灯光是不是会按时熄灭,就像我们不知道总有人在偷偷地爱着你。然而,印象中最美的画面还是妻子带着女儿敲开办公室的门,女儿稚声稚气地说,“爸爸,我们该回家了”。
一路说说笑笑,路灯下我们的影子很长很长。
时光的河,总归要入海流,我们也会在下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相逢。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如此这般,已经很好。
失败者的独白
写完这样一段文字时,我的两个女儿还正在熟睡。作为一个“青椒”,我肯定是失败的。与我那些年轻有为的同事相比,教学什么的很难评价,但在科研方面我的表现实在是过于差劲。就在我们学院,且不说又能搞摇滚又能发顶级刊物的神人C,就单说说跟我私交甚好的同事W。现在的他也已经厚积薄发,当年不被理解的冷门领域现在变得炙手可热,提到这一研究领域必定绕不开他的智识贡献。而且他是真心热爱学术,他的认知实验特别烧钱,按他的话说,老婆让他换车的钱已经被他烧在了实验方面。有时也接点横向课题,挣点小钱,“以贩养吸”。换作我,我肯定做不到的。欣喜的是,这样的努力没有被辜负,他在经历转型的阵痛后也收获了华丽的转身,我也由衷为他高兴。
照此看来,如果不经历一场阵痛,这样的失败或许还将持续下去。我既不聪明,也不勤奋,有时更是将此种失败归于命运的不公与生活的困顿。有时也抱怨为何自己喝凉水也塞牙,有时也干脆走一走时下流行的佛系风格。但我也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肯定不是被生活所绑架最厉害的那一位,生活向我所提出的赎金肯定也不是最高的。
光阴逆旅之中,匆匆过客如我,还是得继续走下去。不敢病,不敢死,不敢说就这样放弃了。的确,有的时候我放下手中的铲子就得到教室拿起粉笔,有的时候夜深人静了坐得屁屁疼(PPT)还得再温习一下要讲的PPT。只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川籍学术民工而言,眼看自己也快油腻了,也该用保温杯泡枸杞了,更喝不下各种鸡汤或伪鸡汤了。青椒肉丝这道经典川菜什么时候才能被我端上桌呢?“青椒”或已老,肉丝尚未齐,酸甜苦辣麻,谁解其中味?
前些日子,陪妻子在学校旁某寺庙爬山时,数次经过的地方之外竟藏着另一方天地,竟然有弘一法师的铜像与他那句著名的“悲欣交集”。又在不久前,听到一首特别的闽南童谣《鱼歌》,女儿以后也会常常央我去菜市场买她爱吃的鱼吧。其中,也有几句歌词特别喜欢,照录于此:
“天有多大/海有多阔/
讨海的人/赶潮落水/
希望有鱼来入网/
天有多大/海有多阔/
保佑大船顺风驶入港。”
也许未来有那么一天,我将不会再如此失败,也会“渔货满满/真多担”。
悲观主义的土地上,会不会开出乐观主义的花朵呢?
而这一天究竟还有多远呢,又有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