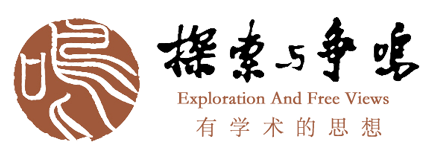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一个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
袁超
内容摘要 本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理论上可理解为要基于国家-社会关系之上,突显并提升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以实现“强国家”建设。具体而言,针对政经关系调整而展开的“经济性分权”是本轮改革的重点,却遭遇因地方政府间“共谋”行为而得以强化的地方保护主义。“司法中央化”有利于通过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来防控地方保护主义,推进“经济性分权”。
关 键 词 强国家 司法中央化 经济性分权 中央-地方关系 共谋行为;
作者 袁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基金项目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度课题项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政党能力: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尝试性分析”阶段性研究成果(CCPDS-FudanNDKT13052)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可谓举世瞩目。笔者认为,本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理解为要基于国家-社会关系之上,突显并提升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以实现“强国家”建设。“改革60条”突显的重点改革应是针对政经关系调整而展开的以“经济性分权”为核心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总体来说,中央政令不畅是“经济性分权”遭遇的首要阻碍,这与因地方政府间“共谋”行为1而产生的利益藩篱不无关系。对此,“改革60条”从基本经济制度、政府职能、财税体制、法治等各个方面展示了多管齐下的治理决心,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司法方面的相关论述与改革路线,并尝试性地将其概括为“司法中央化”,认为这是一种以“集权”(司法集权)方式来推进“分权”(经济性分权)的策略应对,须对其深层逻辑加以研究。
基于上述判断,这里提出本文的中心命题:“司法中央化”有利于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推进“经济性分权”;作为一种动态结果,“经济性分权”在政治过程中也将反过来成为破除地方利益藩篱的原因。
《决定》提出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辅以“改革60条”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其理论内涵是:在国家-社会关系之上,突显并提升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以实现“强国家”建设。“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和“强国家”皆为国家主义学派常用的分析概念,笔者认为对于理解改革总目标的内涵有一定帮助,因此,将尝试运用国家主义视角辅以解释。
国家主义范式以“国家”2为起点,强调国家的重要性,但区别于国家决定论,国家主义者将“国家-社会”关系作为中心展开研究。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找回国家》一书中提出:“对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必须基于一个全面注重其关系的研究方式。”[1]这样一种方法意识与现实指向在该范式的核心概念——“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3中都尽显无疑,它们都是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进行定义的[2]。简单来说,国家主义范式有三个重要命题:第一,国家因其所处的特殊位置而产生特殊职能与意愿。国际无政府状态(international anarchy)使得军事竞争时刻存在,因此国家因安全担忧而成为独立行为者,潜在地具有国家自主性;第二,国家自主性决定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社会制定政策,国家能力则决定国家是否能有效通过社会进行政策执行;第三,在一定条件下,国家自主性与国家-社会关系共同构成国家能力的基础。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曾在其对于日本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研究中做出过精彩分析。他提出用“中心化程度”(degree of centralization)和“区别程度”(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这组概念来分析国家、社会以及二者的关系,前者是对国家、社会各自组织性程度高低的描述,后者是对国家与社会联系紧密程度的描述。国家中心化程度高意味着自主性强,社会中心化程度高意味着社会中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组织凝聚力强、利益涵盖性广,能够高效整合社会并代表社会行动。区别程度低表示国家与社会之联系紧密,互动频繁。他的结论是,在日本应对石油危机的决策与政策执行过程中,国家起了主导作用,整个政治过程是建立在国家、社会的中心化程度高和两者区别程度低的基础上的。该研究同时表明,国家自主性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日本国家能力的基础。[3]
对国家主义范式核心概念、基本命题和研究案例的简单回顾有助于挖掘和理解本轮改革蓝本背后的深层逻辑。不难理解,中国为了应对新形势下国际国内的双重挑战决定启动全方位的深化改革,但关键是如何解释这场改革的指向与推进逻辑。笔者认为,《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这指向政经关系调整),“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本质上要求政府权力从市场微观运作中退出而加强宏观政策调控,相应政经领域的改革可概括为对市场权力保障的(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公民经济权利等为主)同时对政府权力限制(以职能转变、司法体制改革、反腐败等为主)。做好宏观政策制定与政策调控要求“自主性”,确保政策执行则离不开“能力”,要求政府职能转变与限制政府权力实际上内在地指向保证自主性和增强能力。简单地说,政府职能转变所涵盖的政绩考核体系、市场准予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大部门制等将组织内部结构、制度环境产生影响,并尽可能对过去行政性分权造成的非预期结果进行补救,弱化地方政府的微观经济管理权力,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而限制政府权力则直接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产生影响,除了政党权力序列、行政权力序列的反腐之外,本次《决定》提出的“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十分关键,笔者将其概括为“司法中央化”,通过国家统一行使司法权来限制政府权力是法治的必经之路,后文将详加阐释。
因此,《决定》提出的全面改革总目标可理解为建立一个同时具备强国家自主性和强国家能力的“强国家”。然而,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不一定保持一致,还必须考虑国家与社会关系。笔者认为卡岑斯坦提出的“中心化程度”和“区别程度”有一定解释力,但在中国视域下,对国家-社会关系这一研究对象须做出特别解释,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从支配资源的自由度和政策制定的独立性来看,中国具有较强的国家自主性,集中表现为中央能够根据不同时局高效出台相应政策,比如本次《决定》的制定出台,当然这是就现实政治而言做出的判断4。政策框架一旦成型,进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政策细则的制定与推行,前者涉及微观技术问题,本文不做处理,而以政策推行的政治过程为研究重点。进入到政策执行过程,关键就得看国家能力了。要进一步理解中国语境中的国家能力与改革推进逻辑,需要结合重新定义的国家-社会关系。
第二,从危机应对政策的决策-执行过程分析,中国国家政策的执行在国家-社会关系之间还必须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这一关键变量,要将中央-地方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进行叠加分析。相对于卡岑斯坦研究的推行地方自治制度的日本,国家、社会中心化程度高并配合有积极互动的国家-社会关系就能够使得政策有效推行,在中国则面临着非常不同的情况。中国的国家结构与制度环境决定了国家政策在社会的执行需要高度依赖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自身的既有利益,需进行利益计算并与中央博弈,而地方政府与社会建立的联系也常以“指令式”替代“商讨式”。但这并没有否定政策制定过程中以利益吸纳为主的宏观国家与社会互动,即便制度化的上下互通渠道还有待完善,但党中央的决策还是透过其强大的组织力量与适应性将社会新诉求及时反映到国家战略与政策中,以一种单向吸纳来实现国家-社会的利益互通,比如“三个代表”在当时对一批私营企业主等新兴社会阶层的吸纳等[4]。
简单来说,政策执行管道畅通与否直接限定了本轮改革的推进逻辑。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地方政府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关键变量,它处于中央-地方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叠加的中心地带,同时涉及政治权力关系与政经权利关系。在中国基本政治经济生态不变的前提下,市场化改革将总体上为地方市场带来利好,而可能对地方政府不利,因此便遭遇了政策执行的阻力。由此不难看出,《决定》的推进逻辑是要进行不可逆转性的“经济性分权”,既通过配套领域改革来破除地方利益藩篱以推进“经济性分权”,同时又预期借“经济性分权”的不可逆转性从根本上调整政经关系。
“经济性分权”是一种与“行政性分权”相区别的分权策略,它会改变权力的性质,是政府与市场权力在合理区间内此消彼长的过程,具有不可逆性。结合《决定》的具体内容,可从三个维度加以理解:第一,宏观政治-经济关系的维度。指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主要以资本所有制和产权制度为核心,还包括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第二,中观政府-市场关系的维度。指涉及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开放型新经济体制的构建,主要以完善市场规则、市场定价机制、放宽准入为核心,还包括自贸区建设、金融市场建设、城乡统一用地等问题;第三,政府自我规制的维度。主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强调政府减少对微观市场活动的干预。
“经济性分权”本质上是在进行经济利益的调整,在主体意义上则意味着中央-地方关系与政府-市场关系的重构。然而,在美好图景的背后却潜藏着强大的改革阻力,它与长期政府体制所塑造的制度环境和官方历时性的“行政性分权”密不可分。“行政性分权”是指中央行政机关向地方行政机关下放事权和管理权,这项始于1978年的改革策略,通过计划权力下放(物资管理制度、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从统收统支“一锅饭”模式到“分灶吃饭”模式、分税制)、金融体制改革(央行系统与专业银行、国有四大银行系统的建立)、外贸经营权下放和非均衡的区域政策(东部重点、梯度推移的区域政策),使得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极大地享有了自主权,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经济格局。但与此同时,这些改革尤其是“分灶吃饭”财政和非均衡的区域政策引发了中央-地方之间、地方相互之间的矛盾,形成了“诸侯经济”格局,培育了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5]“行政性分权”是诱使地方政府追逐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关键因素,但真正根源还在于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及其主导形成的政企关系,即“经济性分权”要调整的核心关系之一。
更具体地看,地方保护主义在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下得到支持与强化,即地方政府间“共谋行为”。“共谋行为”这一分析概念借鉴自周雪光的研究论文(下简称“周文”)[6],用以分析这样一种行为:“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指令时,一些基层上下级政府常常共谋策划、暗渡陈仓,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予以应付,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周文将“共谋”视为一种中性行为,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是由基层政府所处的制度环境导致的,常常是近年来政府改革中各种理性制度设计所导致的未预期的后果,具体可概括为三个悖论:(一)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悖论;(二)激励强度与目标替代的悖论;(三)科层制度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人缘化的悖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个悖论是关键所在,组织决策的一统性忽视了地方的具体环境,迫使执行过程增加了灵活性,从而为共谋行为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因此,共谋行为是中央集权决策过程所付出的代价。笔者尊重周文的命题与结论,但在借鉴其分析概念的同时要围绕三个问题做相应说明:
第一,关于“共谋行为”概念的借用问题。周文中所涉及的政策单一性与地方多样性问题,在现实政治过程中是难以得到完美解决的,因此中央出台的政策多以指导性框架为主,比如《决定》中的“改革60条”。从这层意义上看,本文以宏观主体(中央政府与以省市为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执行为中心视角,重点探讨中央-地方关系层面上,地方政府对中央宏观政策的认同判断与推进阻力问题5;而周文以个体(县乡镇政府及其官员)为中心视角,重点关注的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微观主体间的问题,它所提到的“政策偏离”更应被置于微观的“政策接受-执行”过程中加以考察,指向个体利益差异化(比如县、乡政府之间,不同级别官员之间)与统一指令式压力共同作用催生的政策执行结果。针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心理,组织势必会做出相应行为,因而上述差异并不影响笔者将“共谋行为”引入到更高分析层次(以省市为主的地方政府)的尝试,但仍需对其内涵做相应调整。
第二,提升并扩展“共谋行为”分析主体的层次与内涵。笔者认为三组悖论实际上共同指向基层政府(作为整体的政府组织和作为个体的官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在不改变“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实质内涵的基础上:首先,尝试提高“共谋行为”分析主体的层次,即从“以县乡镇一级为主的基层政府”提升为“以省市一级为主的地方政府”;其次,尝试使用“政府”的广义内涵,即将地方法院、检察院考虑在内,关注地方行政机关与地方司法机关之间的“共谋”关系。简单地说,这种尝试在理论上假定了司法机关是防止惩治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行为失范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但如果在实践中因法检机关自身系统或是与行政机关形成“共谋”关系,那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这种制度化非正式行为的非预期结果,即由权力勾结与滥用导致的国家权力资源耗散、市场社会权利掠夺等。
第三,本文研究“共谋行为”的逻辑指向。从中性意义上理解“共谋行为”对全面客观解释地方政治过程有重要帮助:同时关注地方政府在应对中央政策过程中的“灵活变通”情形与地方保护式的失范行为。前者主要指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特点对中央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本地情况,本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形式上灵活多变;后者主要指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方利益,侵扰市场(地方政府广义视角)与司法(地方政府狭义视角,即专指行政机关)。由此观之,本文在这一层次上的现实关怀是寻求对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规制之道。“问题二”提到关注地方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共谋”关系的理论担忧,恰恰现实更加严峻:中国的地方司法机关自身还深陷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困境之中。
常识告诉我们,无论从制约个体(包括组织个体和成员个体)天性的角度,还是制约部门权力机制的角度,都必须充分重视以宪法法律权威落定、司法机关设置、司法权运作为核心的法治建设。唯有独立逻辑的权力之间才能形成真正的制约,任何来自个体自觉或是权力逻辑内部的监督都不能稳定并持久。因此,必须通过激活司法权的国家性来真正释放司法权能,具体则要求通过组织结构调整(司法垂直管理)首先打破地方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间的“共谋”关系,然后透过司法权的国家运作来规制以行政机关为主的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6。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倾向于提出以下分命题:推进“经济性分权”面临要破除因地方政府间“共谋”而生的利益藩篱这一难题;由国家统一行使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司法权力才能有效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
“司法中央化”是与“司法地方化”相对的概念,指通过在司法系统内实行财政、人事等方面的垂直管理,使司法权高度集中,摒除干扰,由国家统一行使。
从理论与经验来看,“司法中央化”意味着国家性是司法权的根本特征。“中央化”是在中央-地方关系上这一层次上的论述,法学学者对此也有相同的主张,认为司法权应当是一种中央权力。根据审判级别和管辖范围的不同,国家性的司法权在形式上需要由地方法院行使,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适用统一的法律规范,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仍以国家性为根本特征。[7]哪怕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分权社会,司法集权也是尤为重要的,美国政治鲜明地展现了这一点,关于这一问题,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早有精彩论述,他认为美国联邦制使得州能够高度自治,每个州之于整个联邦不仅形同外国,而且永远与联邦对立,如若容许各州法院执行联邦法律,那就等于把国家交给外国法官审理,这样的制度于理不合,有悖经验。因此,美国创立联邦司法当局以实施联邦法律,将全部司法权掌握在最高法院手里,为了便于审理案件,这个法院又设立一些下属法院。唯有联邦最高法院受权解决与法院管辖权有关的一切问题,并在各州大权中居于高位。[8]尽管中美两国的国内政府间关系不同,但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一致的,司法权集中于国家共同指向以国家力量确保司法权威,防止因司法权力被行政权或地方政府绑架而耗散国家资源与权力,侵蚀社会权利,甚而引发整体性的治理危机。
从司法实践来看,中国的司法机关不仅不能有效防控地方保护主义,反而深陷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困境之中。《宪法》第12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第13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工作,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工作。尽管最高检和最高法在理论上可以监督各级工作,但实际上由于能力所限只能通过司法解释的统一适用来笼统地产生影响,在地方司法过程中难以真正奏效。其制度根源再明显不过了:地方政府控制着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与人事,使其毫无独立性,更妄谈自主性。这尤其体现在本地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中,地方法院往往在判案中偏袒当地政府。此外,地方各级司法活动与地方党委、地方人大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司法判决有时不得不考虑当地党政领导的指示或意见。从组织意义上分析,司法机关丧失财政、人事权则意味着司法机关完全被“绑架”,那么地方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间的“共谋”关系就因此被强化了,更关键的是,司法机关独立性的丧失直接导致其在“共谋”关系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机关利益事小,司法权沦陷则可能成为万恶之源,随之而来的或许会是社会公正丧失引发的信任危机、行政权力失控导致的秩序危机以及地方司法权无效导致的国家司法体制整体性危机等。2003年发生在河南洛阳的“种子案”[9],“本来是地方司法捍卫国家法治统一的正面典型,但是其后的发展却凸显了地方法院的困境,并为积重难返的地方保护主义提供了新的注脚。”[10]
“司法中央化”对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规制作用可围绕司法权的功能展开分析,主要体现在两条逻辑上:第一,从“司法中央化”的组织意义上看,通过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权上移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去除地方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地方化,恢复其应有的独立自主性,从而直接消除地方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等进行“共谋”的组织惯性,实现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等行为的监督自觉;第二,从“司法中央化”的权力运作意义上看,依附于司法组织的司法权力集中于中央,使得这一权力在位阶(国家性)和性质上都能够独立于地方行政、立法权力,真正实现“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约”,如此才能够将作为一定程度上自主利益体的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限定在法治轨道之上,发挥其“灵活变通”的潜力,惩治其失范的利益行为,同时还包括利用司法权威维护法律尊严。
出于对全面启动“经济性分权”可能遭遇的阻力类型与程度的判断,“司法中央化”终于如此明确地进入到政策执行日程,《决定》中“人财物统一管理”与“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表述直接针对地方司法机关独立自主性问题做出了宏观定位,无比鼓舞人心,但制度改革的推进结果究竟如何,仍有待观察。对于此项改革,有学者提出,在条件成熟之时,还需进一步明确改革路径,“像人民银行(央行)体制一样,做到司法权力的国家性管理”[11],笔者对此深表赞同,这理应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中之重。
“经济性分权”向我们展现的是一幅理想的政经关系图景,它是一个理论近似值,在现实中可能无法精确实现,但却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来无限地动态趋近。集权与分权是可供选择的改革策略,它不是必然对立,更不应有绝对的价值判断。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先发国家大多通过分权成为发达国家,而后发国家则更多是通过集权而实现飞跃。但哪怕是几乎获得公认的基于公民社会建构起现代国家的英国,也有研究证明在其现代国家建构最关键的公元1000到1760年七个世纪里,有大约70%到90%的国家财富用于军事用途[12],那这究竟是代表着集权的国家促进了现代化,还是强调分权的社会实现了现代化?以一条简单逻辑看待历史经验,一定会掩盖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同样,中国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也不是单用集权或分权概念能够解释清楚的,基于本文的分析,此次改革的推进逻辑最起码是深含运用集权策略推进分权改革的意味,比如通过“司法中央化”(司法集权)防控地方保护主义,破除地方利益藩篱,协助“经济性分权”。
逆向来看,“经济性分权”指向的政经关系调整将实现权力性质上的终极转变,即政府权力边界后移的同时,将微观经济管理权转变成为市场自治权,充实市场权力。逻辑上讲,当市场能够相对自主地开展经济活动,而政府仅限于通过宏观调控来保护产权、维护公平,警惕市场失灵时,也将从根本上有利于推进包括司法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本文中使用的“共谋”这一分析概念借鉴自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一文,但对其分析对象和结论解释有做一定调整,后文将详细阐述,特此说明。
2国家主义范式中的“国家”是组织意义上的国家,被看作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具体可参阅西达·斯考切波(ThedaSkocpol)的相关著述。
3斯考切波认为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是指,国家作为掌握一定领土和民众控制权的机关可以制定和追求并不简单反映社会组织、阶级或整个社会的需求和意愿的目标。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是指国家执行其正式目标的能力,尤其是在面对力量强大的社会组织的实际或潜在的反对时,或者是在一个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参阅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9.
4在现实政治中,全国性的政策无论出自一个由统治阶级领导的国家组织,还是完全掌控了国家组织的政党组织(比如中国,党中央是决策中心,国务院相对而言只是执行中心),它都可被看作是国家政策,整个政策过程作用于地理疆界意义上的国家,不影响宏观分析。相对于现实政治,即为理论政治。从后者出发,对于国家自主性强弱的判断还需更为深层次的考量,最起码要先判断国家形态问题,是民族-国家还是政党-国家,这决定了国家组织究竟以怎样的地位存在。该理论问题不是本文要处理的,在此只做简单说明。
5比如中央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地方招商引资问题的政策调整都会在现有绩效考核体系下影响地方政府整体或个体官员的利益,那么地方便会形成对该政策的认同判断,有较强地方自主性的省市(比如上海、广东、浙江等)会相应选择积极配合、消极怠行,甚或拒绝执行。
6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前文关于“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是不可能根除的”这一论断是基于行政权的地方性做出的。然而,因为司法权独具国家性,它应该同时具有非地方性和非行政性,在组织意义上就是司法机关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所以理应可以完全消除地方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共谋”关系。
[1]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0.
[2] Karen Barkey and Sunita Parikh,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state.” Annual Reviews of Sociology, 17: 523-549,1991, pp.545-6.
[3] Peter Katzenstein, “Conclusion: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edited by Peter Katzenstei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4]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 杨光斌:《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110-120页。
[6] 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7] 王旭:《论司法权的中央化》,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
[8]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4-184页。
[9] 郭国松:《法官判地方性法规无效:违法还是护法》,载《法治与社会》2004年第2期。
[10] 张千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防治机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1] 杨光斌:《走出集权-分权二元对立误区——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集权与分权问题》,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
[12]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Ⅰ: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