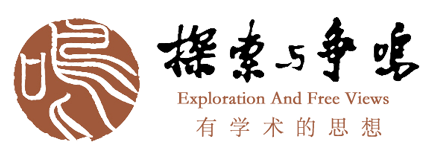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台湾地区地方派系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桑玉成1舒翠玲2
内容摘要 派系是台湾地区政治中较为独特的政治现象。国民党退居台湾地区后,在台湾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基层组织,重塑了台湾地区的政治派系生态,甚至形成了所谓的恩庇侍从体制。随着政治转型,台湾地区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生活习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政治派系模式和政治生态结构瞬息万变。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地区政治派系呈现出三种变化态势:一是逐渐瓦解殆尽,二是逐渐减弱、分裂或移转,三是逐渐凝聚与强化。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台湾地区政治派系与政治生态的发展演变是同频共振的,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是理解台湾地区政治的重要观察窗口。
关键词 台湾地区 地方派系 政治转型 派系政治
作者 1 桑玉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 舒翠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上海200433)
在现代政治研究中,派系与派系政治往往不大受到关注。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派系在政治过程中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某些地区或某些特定情况下,政党积极利用派系作为其政党活动的补充,还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台湾地区是派系相对活跃的地区,尤其是在政治转型以来,台湾地区的派系政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研究台湾地区地方派系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当能够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台湾地区政治的形态及其走向。
台湾地区地方派系及其起源
台湾地区是比较特殊的地方政治形态。在台湾地区的派系政治中,地方政治人物往往以地缘、血缘、宗族或社会关系为基本结构,聚集结合,以争取政治利益的组合。以选举、议会等为主要活动场域,具有在地方政治上决定选票、推荐人才影响选举与决策的功能。而同时台湾地区的地方派系虽因为风俗民情及人际连接而有相同之处,但是却因为每个地方的经济与政治条件不一,派系人物作风与人格特质不同,展现出每个不同的地方派系的经营方式与风格。
因此,台湾地区地方派系是按照人际互动关系所形成的社群样貌,经由人情义理、文化与风俗的结合,加上政治和经济条件的互补,所形成的一个集政治、经济、利益与感情的多元价值所统整的组织群体。
台湾地区地方派系具有以下特点:1地域性。2初期地方派系的形成通常是地方上的政治精英相互竞争的结果。3台湾地区的地方派系多数都可以指出派系领导者。4地方派系主要的活动场域为参与政治性选举,次为准公部门如农、渔会等职位的竞逐。5台湾地区早期政党发展中,地方派系几乎都是依附于国民党。依据调查,台湾地区地方派系按层级的不同可以分为:派系、桩脚、民俗网络。此三种网络层级能使派系成员运用人情压力,有效动员派系成员与基层选民。
派系不只是一种统御模式,也不只有一种社群关系,派系除了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分配外,也有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决定的力量。这样看来,应该将地方派系定义为一种地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地方派系与社群网络一样,也同时兼具“拟似家族团体连带”和“情感与利益加权关系”,以及不同层级政府间“包容式行政”的色彩。
有关“地方派系”的源起,一种观点是比较人类学的“自然发生”论述,另外一种则认为地方派系是外来政权故意创造的。[1]认为地方派系是外来政权为了便利统治所故意创造的,以学者吴乃德的论点为代表,其认为“地方派系”建基于国民党的“恩庇侍从主义”(patron-clientelism),这是两种政治精英的搭配。国民党在低区性的选举,召集地方人士投入选战,成为与自己相同理念的党员,以维护自己的政权正当性,而且利用了地方派系在选举制度下能互相抗衡的功能,作为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学者赵永茂,虽然他没有明示地方派系为国民党所创造,但他明确指出地方派系是战后因应地方选举而出现的政治现象[2]。
持地方派系自然生成看法的布鲁斯·雅各布(Bruce Jacobs)则没有明示派系生成的时间。[3]倒是历史学者吴文星认为,台湾地区的地方选举和区域政治职务(参事、区街庄长、保正、甲长、府评议会员、各级协议会员)大约在1920年代开始,因此地方派系是在日本统治时代就已经形成。[4]
研究者大致上可以对台湾地区地方派系的形成时间达成共识,即地方派系的分类结构始于日治时期的社会阶层分歧,但到了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因为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地方派系由此从中壮大,成为恩庇侍从体系的一环。问题是,战后的台湾地区面对二·二八事件及其后清乡的打击,大量的本土精英消失[5];然而吴乃德和陈明通认为战后的地方精英,与战前的社会政治参与者有相通,但是二·二八事件之后,许多县市参议员在面临社会的重大动荡后,八成以上的政治精英消失于政治领域。[6]吴乃德和陈明通的看法,奠定了台湾地区“地方派系”研究必须与战后国民党统治技艺相联系的基础,其中或许有战前社会分歧的历史基础,但那并不影响战后派系运作的逻辑与国民党的统治技艺。
台湾地区地方派系的发展
台湾地区的地方派系发展,一直是近代政治学研究的焦点议题。吴乃德的“恩庇侍从体制”当然是最受瞩目的看法,他的控制与动员说,深刻地影响了台湾地区地方派系研究的方向,诚如研究国民党选举机器的任雪莉所指出,吴乃德的博士论文是至今关于台湾地区地方派系在选举动员的描述上最权威完整的作品。事实上,以后的研究者无论是王金寿讨论侍从体系崩解,还是赵永茂以高雄县内门乡为例去分析乡级地方派系在几十年来的选举动员结盟方式,陈华升讨论县级派系和乡级派系之间的动员关系,甚至王振寰谈民主化后国民党如何引导国家机器转型[7],都不出吴乃德的控制与动员论述。
国民党一直以来利用党的力量和地方派系同时深入本土社会的最基层,以作为其统治的手段及基础。虽然无法证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的动员中,党的力量可以超越地方派系的力量去控制投票结果,但辅以吴乃德教授点出的“空降”案例来看,国民党的党部机器在“控制”地方派系上,当有成功的影响力量。
国民党之所以在台湾地区能建立庞大的组织,其深入基层的过程一直被人关注。通过国民党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台湾地区派系的一些发展轨迹。195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建立了统治基础,并通过动员戡乱体制、戒严、实施党禁、舆论检查、学校教育控制等手段,建立了一套威权体制。这种结构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党领政、以党领军,党对政权机关进行监督指导,对社会实行全面的控制。
初期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精英用有限的地方选举加以笼络,要求当选的地方政治精英加入国民党,希望以党的力量来规范之。同时,以“区域性的联合独占经济”的诱因笼络地方派系,包括信用合作社、农会信用部门、渔会信用部门、汽车客运公司等。为防止反叛者的政治活动形成有组织的反对势力,领导者运用了两项手段,一是禁止候选人的选举同盟,另一方法是禁止新政党的建立。
1970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党主席、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自觉政权稳固,已无其他势力可抗衡,因此想铲除地方派系,全部选拔重用来台之后所栽培的党工干部,以便完全控制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20个县市的选举中,国民党提名了17位不具派系偏好的县市长候选人,这种排斥派系的拙劣、私心的手段,反而引起了地方势力的反弹。因此,这次选举结果是国民党失去了四位县市长席次(台中、台南、高雄、桃园),并引爆了一次反抗威权的中坜事件。并且在美丽岛事件之后,开始了反对党人士参政与公开竞争的机会,促使政府逐渐开放,一步步走向民主化与本土化,终于在1987年解严,结束了国民党长期的威权控制。
1980年代,台湾地区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反对党成立、立法机构全面改选,对国民党的执政带来威胁。其他政党都想推翻国民党,真正取得执政权,因此选举过程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为了继续执政,便加强了与地方派系的合作关系。政治转型之后的反对浪潮兴起,社会动员与控制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容易,由上而下的动员控制能力逐渐式微,而由下而上的草根动员能力却日益增强。在权衡之下,国民党只好利用黑道关系,引入桩脚动员系统。黑道人士也想通过选举洗白,甚至是维持黑金事业的发展,希望在取得行政资源后,对自身的特种行业进行庇护,放松取缔非法营业,利用对警政机关进行质询监督、控制预算给予压力,为他们所经营的事业护航。“反黑金政治”成为反对党强力的要求。
当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地方派系与选举之间的关联性时,也是着眼于地方派系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些研究派系的学者关心的方向。例如朱云汉与陈明通对于国民党以区域性独占经济、公营行库的贷款、政府采购案以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笼络派系持续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研究[8],广为学者引用。王振寰就在这个基础上,以国家机器的概念继续讨论1992年立法机构全面改选后,地方派系的力量如何往上层扩张,扩大其经济资本[9]。陈东升在《金权城市》中也表示出类似的观点,认为土地重划利益赤裸裸地影响台北地区的地方政治,并成为地方派系挥军台湾地区政权的雄厚资本。
政治转型如何冲击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的政治受到重视,派系的反扑有时也确实冲击了国民党的统治能力。但随着政治转型的进程,地方派系面临新的处境。王金寿指出,国民党为了维系政权所建立的侍从体系已经招致破坏,不只是侍从体制在分解,依赖侍从体制而生的地方派系也因为政治转型的脚步而逐步崩溃。越到后期,国民党不只买票机器失灵,地方派系也变得不听指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地方派系与侍从体制通通崩解了。[10]
徐永明和陈鸿章就用量化数据呈现岀1980-2000年之间的地方派系和国民党与选举的关系。他们认为,1980年代地方派系呈现了“选举效率增长”与“深化政党”的形态;而1990年代的地方派系则呈现了“选举效率衰退”及“深化政党”的形态。也就是说,地方派系与国民党越来越水乳交融,但派系在选举上却面临反对党的强力挑战,开始有动员失灵的现象。[11]某种程度来讲,徐永明和陈鸿章认为选举机器失灵的同时,国民党和派系之间的互赖却越来越深。
台湾地区的地方派系没有正式的运作规章,也没有明确的界定范围和稳固的选举人,但是它以共同的利益结合人际关系,影响政策分配的过程,因而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利益团体的雏形。
然而,地方派系是过去传统农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人情”“自我价值”“地方归属”等非正式组织、小团体所延伸出来的社群团体概念,随着社会形态的迅速变迁,地方派系从缜密逐渐走向松散及削减[12]。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派系模式发生了变化。教育水平的提升、都市化的发展、媒体的革命性变革、信息传播的迅速、人口流动的频繁,以及小型社区如雨后春笋到处林立,人民得到政治与其他方面的资讯管道五花八门,因而有可能培养出具有“政治效能意识”(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拥有更高的政治素养与自主的选择权,这样的进程发展与过去传统农村所看重的见面三分情式的互动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有学者发现,派系发展的现实状况已有改变。在一项研究报告中,偏僻或者都市化较低的地区,较难形成派系。而在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民自主性高、人际互动频率弱,同样也缺乏派系动员的条件,因此地方派系网络的建立也很艰困。相较之下,处于中间形态的地区——现代化与都市化发展中期的区域,既具备足够及便利的都市利益,同时还存在派系发展所需的人际网络,反而在这种地区内,地方派系政治的经营是最容易的。
派系与派系政治的发展及其走向
在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皆发生了如此巨变的情形之下,地方派系以及派系政治,在1980年代中后期至2000 年代后期的20余年间,可说是台湾地区政治学研究相当醒目的显学。不过,这股传统的地方派系研究,在2000年后因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过程中国民党下台,改由民进党执政,遭逢重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地方派系研究议题则是执政的民进党和各地方派系之间会产生怎样的互动关系。根据近些年来台湾地区学者关于派系问题的研究,对台湾地区派系以及派系政治的走向大致有如下一些看法。
一是,瓦解殆尽的地方派系。过去,国民党为了巩固统治根基,使用及控制寡占性经济资源,作为安抚、拢赂与奖赏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型的地方派系。然而政治转型之后,当国民党充当“恩主”的可能性日益减少,不再具有利益交换的优势,尤其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通过一连串的立法斩断了地方派系赖以维生的钱脉来源,例如围标政府公共工程、规范政治资金等。加上近年来不断独立的司法体系、查贿、肃贪,使得地方派系“买票”技俩和管道受到重创。以至于政府和派系之间的从属结构松动甚至瓦解,派系在后续的选举角色扮演中也逐步失去了它的功能性。持上述类似主张的王金寿,在几次选举观察和深度访谈屏东县地方派系之后,认为以屏东为例地方派系几乎已经瓦解殆尽。[13]他认为这个现象凸显出过去对于地方派系的研究成果将不再适用于现今的地方政治状况。再则在新的选举制度改革之下,虽然派系之间拥有合作的可能空间,但派系间相争的“路径依赖”依然存在。林文斌认为在基层政治中出现了“双重侍从关系”,即地方派系领导人和成员间形成的“侍从关系”,以及国民党与地方派系通常夹带着利益交换关系的另一种“侍从关系”。[14]
二是,逐渐减弱、分裂或移转的地方派系。另有一派学者认为威权体制的崩解、民主转型的成功,社会经济程度的提升,同时都市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化的人际关系趋向疏离,再加上二次政党轮替的形态巩固之后,地方派系的权力结构、运作方式与政治制度的变化、政党之间的互动,都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渐渐地由单纯的一党独大下的派系山头掌控局面,转变为复杂的派系山头间的竞争、重组、结盟或走向政党之间的竞争。另外,派系上层是以利益为最主要的考量,而有些派系的基层则是以感情、主张与理念而产生的向心力与忠诚感,在感情、主张与理念无法被满足甚或被出卖的情形下,投靠其他的派系或组织,或者退出派系与政治活动,这种种情况也趋于复杂化。而此时,基层群众的心声、情感若找到了可以替代的对象,脱颖而出的组织、团体因缘际会也可弥补出现的政治空隙。因此像传统国民党地方派系的动员管道,如农会、水利会、信用合作社及黑道,都已经随着政党轮替、政府政策以及社会发展、经济成长等外在环境变迁,逐渐失去或降低选举动员的能力。
台湾地区的地方派系根植于本土社会的文化结构,如利用血缘、姻缘和地缘等传统社会人际网络来建构派系组织。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这种凭借着传统人脉建构的组织已逐渐趋于松动,反而是因应职业、兴趣或专长而新兴的社团组织,例如小区发展协会或者义警、义消等社团组织,其动员力量不断增强,是否取代原来的地方派系山头,其动员及依赖的途径为何,也值得关注。另外,“县长-乡镇市长-调解委员”此种依据行政体系所建构的派系是否将会完全掌控县内的行政资源,也值得后续观察。持上述主张的学者以黄德福等为主。黄德福认为台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以传统人际关系取向为主的地区,随者社会经济生活的快速现代化,应该才是降低地方派系政治影响力的关键所在。[15]王业立指出,地方派系在经过中央及地方政权轮替后,影响力缓慢下降,其领导方式已渐由一人领导逐渐走向集体领导。与政党的结盟方式,也由一派一党逐渐走向一派多党。全县型的地方派系逐渐松动,地方山头型政治人物影响力日增。[16]
二次政党轮替形态巩固之后,地方派系的权力结构产生移转,由单纯的一党独大下的派系山头转变为复杂的派系竞争、重组、结盟或走向政党之间的竞争,地方派系和国民党出现了恩庇者移转的现象,民进党执政以资源释出争取传统上支持国民党地方派系的结盟。立委选制的变革,加深了政党间的对决,地方政治势力由派系间的竞争朝向政党间的竞争。但政党竞争是否能完全取代派系竞争,则仍有待观察。
三是凝聚与强化的地方派系。2000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就国民党而言,地方派系有区域结盟与更“中央化”的现象。尤其是随着选制的改革,立法委员选举采用政党竞争的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立法机构的角色增强,这些区域结盟与高层结盟或次团体、派系化的现象将因此而可能有增强的趋势。就地方派系与外部社会、经济、地缘环境的关系来说,在乡村与边陲地带,国民党、亲民党的派系都有和黑道、金权三位一体化的现象。另外,就民进党而言,随着地方、高层逐渐取得执政权的激励,各派系之间也有新的结盟、串流与扩张,亦渐有由原来理念型派系转而成为接纳黑、金体系与人士的黑金派系的现象,而亦有可能渐渐地成为台湾地区地方派系新生态中的一环。赵永茂就认为,地方派系有区域结盟及更高层化的趋势,尤其随着立法机构角色的增强,这些区域结盟与高层结盟或次团、派系化的现象将有可能会加强,且已呈现若干政党移位与功利移动的现象。而随着都市化与民主化的提升使选民自主性也跟着提升,地方派系掌控的选民似乎逐渐减少,但是在地方性(乡镇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的选举时,地方派系仍然是会对选举结果造成不可忽视影响的力量,尤有甚者亦可能影响全台湾地区选举的结果。[17]因此就更凸显出,对国民党内的派系来说,新的选制(单一选区两票制)反而可以使地方派系的地盘变得更为稳固;但是不一样的却是,原来属于全县型的地方派系,在选制变更后,其地盘的分布转而成为以选区为单位的地盘分布,如此才能便利其于选战中操盘与运作。
参考文献:
[1] 蔡明惠、张茂桂.地方派系的形成与变迁:河口镇的个案研究.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97(77).
[2] 赵永茂.台湾地方派系与地方建设之关系.高雄:高雄德鑫出版,1978:126-143.
[3] Bruce Jacobs. Local Politics in a Rural Chinese Cultural Setting: A Field Study of Mazu Township, Taiwan. Canberra: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0: 160-172.
[4] 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台北:台北正中书局,1992.
[5] 张炎宪等.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台北: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2006.
[6] 吴乃德、陈明通.政权转移和精英流动:台湾地方政治精英的历史形成.赖泽涵编.台湾光复初期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303-334.
[7][9] 王振寰.谁统治台湾?转型中的国家机器与权力结构.台北:台北巨流出版社,1996.
[8] 朱云汉、陈明通.区域性联合独占经济、地方派系与省议员选举:一项省议员候选人背景资料的分析.“国科会”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1992(1).
[10] 王金寿.政治市场开放与地方派系的瓦解.选举研究,2007(2).
[11] 徐永明、陈鸿章.地方派系与国民党:衰退还是深化?台湾社会学,2004(8).
[12] 黄德福.政党竞争与民主发展:台湾地区解严后的政党政治.葛永光等.现代化的困境与调适——“中华民国”转型期的经验.台北:幼狮出版社,1989:95.
[13] 王金寿.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东为例.台湾社会,2004(7).
[14] 林文斌.选举制度改革对地方派系的影响:台湾高雄县的个案研究.地方自治与民主发展:2008年选后台湾地方政治学术研讨会,2008.
[15] 黄德福.现代化、选举竞争与地方派系:一九九二年立法委员选举的分析.选举研究,1994(1).
[16] 王业立.2004年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与立委选举派系动员之比较:台中县的个案分析.“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东海大学政治学系.
[17] 赵永茂.新政党政治形势对台湾派系政治的冲击:彰化县与高雄县个案及一般变动趋势分析.政治科学论丛,20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