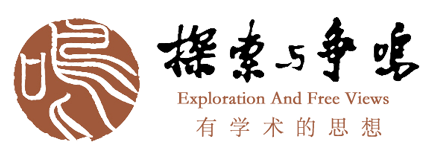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一个流浪的人怎么就成了大师?该反思今天我们怎么做学问
汪涌豪
首先我必须说明,我下面讲的并不是在对大家提希望,而是想和大家共勉。如果过程中指出了一些问题,且比较精准的话,那也是因为我把自己也包括在内了。因为我知道做学问最需要避免什么,所以,接下来我讲的内容绝对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针对在座比我要年轻的学人,而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
这里我想讲三个关系。第一个关系,分业与综合的关系。所谓的“分业”是王国维先生在《教育小言》里面说到的。他认为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分业的时代,比如以前我们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的知识是包罗万象的,今天随着学问的进展,大家分得越来越细了,搞古典学的绝不懂史学,搞文学的不知道史学与哲学。但其实我们看近现代以来,那些大师都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在王国维上述的判断中,对“分业”并没有任何贬义,但他自己显然是关注广泛、善于综合的大家,他在1901年到1907年这个阶段,即所谓“独学时代”,将整个身心都放在了读书与研究上,但他的对象决不仅仅限于文学,还有古文字学、史学和考古等。今天大家研究他的《人间词话》,都觉得这是一部杰出的词学理论批评著作,很少有人讲到其中对德国哲学和美学的借鉴与综合。所以我想说,在当今这个分业的时代,学人尤其需要有综合的视野。
说起来,分业的观点是王国维提出的,但分业的时代早就开始了。《庄子·天下篇》称“道术将为天下裂”,即意识到本来为学论学是混沌的,但后来却日渐走向精细。但这里要特别指出,这种精细化产生的是诸子百家之学,诸子百家之学不是能用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学、伦理学或文学等的分判的,他们的视野开阔,他们的学问本身就是综合式的学问。
所以我们要处理好这一对关系。一方面要做一个专门家,在分业的时代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另一方面始终要有一个综合的视野,因为时至今日,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再单纯,不再有严格的逻辑边界,而是与周围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尤其研究中国当下的问题,更是如此。
现代有一位历史学家叫杨人楩,早年曾写过一本《高中外国史》,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当时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书名不叫《高中世界史》,这样的题目更贴合他作为著名世界史专家的身份,也更加吸引人,更加有气势,立意更高。但他说自己之所以突出“外国史”而不是“世界史”的目的,是因为在撰写此书时心里总有中国史在,他希望别人在理解世界史时,心里始终要有中国在。所以他写《高中外国史》,是将世界和中国比量着来看的。
我想说,其实研究任何问题都要这样,研究东方问题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西方的视角;研究西方的时候,反过来也要有东方的思考。一个学者如果针对一个问题做得很专很深,但没有更广大的视野,那么要达到更高的境界是十分困难的。他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而我们特别需要避免这种极端。
第二个关系,问道与问学的关系。今天我们都是走在问学的路上,学无止境,即使到60岁时,我们的面前仍会还有许多不懂的东西,当我们把知识边际扩大的时候,所知增多,外延面的未知也就更多,纷纭交杂的问题向我们涌来,让我们总觉得追不上。所以,问学是一个终生的过程,这个世界的问题你是处理不完的,但你又想处理或必须处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命令作支柱。这个支柱就是问道。
诸子百家中的《晏子春秋》,各位可能关注不多。里面《问篇》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被我贴在儿子的书桌上,作为他的座右铭:“问道者更正,闻道者更容”,原意是说去问道的人会更正自己的选择,边上听说的人会改变他的神情。当然它有更值得重视的衍伸义,那就是追求道理的人会更加正大,懂得道理的人会更能包容。由于《晏子春秋》没有明确是在哪个意义上用这“正”与“容”的,我们自然可以有如上的解说,并认为这第二种解释相对第一种更有趣,也更有深意。
一个人问学的目的是什么?弄清楚每一个问题,是学人的职份,也是我们兴趣所在,那么,弄清楚这些问题是为了什么?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指出,中国的一切学问都要从它的起因上说起,中国人问学的目的从来是为了问道,不仅从起因到动力是如此,乃至最终的目标也是为问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专注一隅而不及其余,更不关心更广大问题的书呆子。
第三个关系,知道和知识的关系。这个世界,喜欢追求知识的有两种,一种是知道分子,一种是知识分子,知道分子是对自己研究的东西都能通晓,但他仅仅是知道而已。而知识分子则不同,他对所知道的东西不仅止于通晓,更要解构、批判,向这个对象投去自己的光束,使之产生新的东西,这才叫知识分子。所以,千万不要以做一个知道分子为满足,而应以要做好一个知识分子为追求。
知道分子经常在书斋求知,把知识弄得很精细,这自然是好的。但千万不要忘记,知识不是孤芳自赏的玩物。古今中外,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孔子、孟子,哪一个不关心社会发展?风声雨声,国事家事,哪一件不入脑入心。就说此次征文,一等奖获得者研究的问题就和社会现实、国家发展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一个读书人要既能安居书斋求知,又不忘服务社会。书斋求知需要尽量克服受黑格尔批判过的“利害之心”的指使,一定要告诫自己尽量摆脱这些东西,必须时刻不忘自己对社会是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自外于人,更不应傲慢,但他难道不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吗?若他不是,总不见得那个已成网红的流浪汉是。我当然不希望我出去的时候,许多人围着我,但我真的不理解这种现象。这个社会的某些地方是不是生病了?
总之,做学问一方面钻就要钻得非常深透,全身心沉下去;超拨时又要超拨到更高更广大的境界。古今中外成一流学问的人都是同时拥有这两端的。我希望随着学术条件和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我们应该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