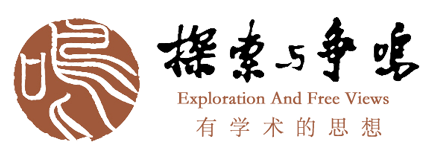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身份的迷思
——当代西方身份政治学的兴衰
郑薇 张亮
内容摘要 身份政治学是左翼力量边缘化后的重新登场,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作为恢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身份信仰而作出的努力。原先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左翼人士出现了身份缺失的现象——要么主动放弃,要么选择“中间道路”。它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资本主义新变化时期,兴盛于世纪交替之际,并形成多元文化主义式身份政治和正义式身份政治两大典型理论形态,有效地批判了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加深的不平等社会关系。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身份政治学的弊端显露无疑,无力回应批判资本主义的激进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只有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议题之中,才可能找到变革资本主义的路径。
关键词 身份政治 西方左派 身份认同 新自由主义
作者 1 郑薇,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2 张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南京2100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MZD026)
身份政治学(identity politics)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后涌现出的多种新的左派理论规划之一,它积极回应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社会的各种身份-认同诉求,是当代西方左派在革命被无限期延宕条件下维持抵抗、表达立场的一块理论阵地。身份政治学发端于20世纪70、80年代,之后不断总结新社会运动实践经验并与后现代理论进行链接,在新旧世纪之交进入兴盛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出现停滞甚至逆转,文化多元主义在欧美遭受质疑、反思和批判,身份政治学也随之进入分化和调整期。历史地看,身份政治学确实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不平等关系的改善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它在本质上是以维护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体制为前提的,因而具有不可持续性。身份政治学的衰落让西方左派再次意识到,只有重新回到直面资本主义体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对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抵抗、批判才可能是真实的,否则只能不断落入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逻辑的陷阱。
当代西方身份政治共识的兴起
在西方,身份-认同问题早在18世纪到20世纪初欧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就出现了。在这个阶段上,身份问题就是对民族身份的辨识和认同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欧盟一体化等的不断推进,民族国家在西方特别是欧洲逐渐式微,原本应当随之退潮的身份-认同问题却不退反进,吸引了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关注。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身份-认同的主要斗争场域已经日益从民族冲突转向移民、地区冲突、极端宗教主义等诸多问题上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说:“身份政治的出现是本世纪(20世纪)第三个25年开始展开的意义重大的社会转型的结果之一”[1]。
身份政治学兴起的历史前提是资本主义已告别黄金时代、进入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2]所谓黄金时代是指摆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停滞、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文化社会普遍繁荣的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发展期,从战后恢复期的20世纪50年代到又一次迎来经济衰退的70年代,大约持续了20年。黄金时代建立起的“福利共识”[3]虽然使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新的多元化的边缘人群,他们被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当资本主义为了应对70年代的社会危机而不得不调整自身之时,以市场化和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新秩序[4]直接冲击原有的社会规范、价值和信仰,使得个体陷入一种孤独与被剥夺的不安全状态之中,失去了维系身份认同的可靠来源。因而,这种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资本主义自身,却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引发身份焦虑。大卫·哈维也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5]。身份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由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所催生的。
身份政治学得以持续发展的政治动力是“后社会主义危机”下西方左派的“自救”意识。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遭遇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实践和理论遭受双重打击。曾经风起云涌的左翼运动急转直下,甚至陷入停滞。不仅如此,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失去信心。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西方左翼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身份政治学就是方案之一。正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那样,“应该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6]苏东事件本质上只是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其中一种社会形态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灭亡。但是,传统工人运动的式微已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成为当代西方左翼运动的新趋势。身份政治以性别、生态和种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运动为基础,包括反种族歧视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具有分散性、多元性和偶发性的特点。与传统社会运动以阶级为基础,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不同,“新社会运动是建立在身份认同基础上的、反对‘权力控制’的斗争”[7]。它们大多都不是以阶级而是把身份作为划分成员的标准,因而形成了跨阶级的多元政治主体,如同性恋者、女性、少数族裔等新兴边缘群体。总之,这场“抵制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社会运动”[8],立足于微观主体与微观政治,用多元抗争取代宏大革命,成为当代西方左翼可依靠的潜在抵抗力量。
西方政党政治体制在客观上助长了身份政治学的影响力扩张。具有左翼倾向的政党常常把身份政治的相关议题作为竞选的策略,期望能重掌政权。1997年英国工党时隔18年的大选胜利,虽不能完全归于少数族裔策略的调整,但不可否认其作为标志性政策方针的选票吸引力。少数身份群体当选为议员的比例不断攀升即可视作身份政治的结果,同时又成为有效扩大身份政治影响的保障。因此,身份政治可以借助左翼政党推进自身的现实诉求,期待政党能兑现承诺。即便是最终左翼政党选举失败,也能迫使偏右翼政党做出调整,以达到身份政治的小部分目的,即便只是战略性的妥协。
与后现代话语的有意识链接,是身份政治学能够在当代西方学术体系中博得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总体性”以及“同一性”进行审判,强调从现代理性和知识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回归日常生活世界。身份政治遵循这一思路,重视个体微观权力,使个人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问题成功占据了理论中心位置。其中,福柯通过对边缘群体的系谱学研究,指认了所有围绕在所谓边缘群体之上的话语都是知识与权力的共谋之产物。以同性恋者为例,福柯指出,当它被界定时,被相关法律、医学知识和机构共同制造时,就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出场。主体性的讨论已被位置生产理论所取代,占据主体位置的个人必须按照预设的规则进行解读。换句话说,“个人可以在社会阶级、出身、族裔以及民族等因素上各不相同,但当他们认同话语所建构的这些位置,使自身处于其规则之下,就成为权力/知识主体,从而获取意义”[9]。身份政治吸收、利用这一理论,表明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控制是通过话语建构完成的。不仅以知识体系的形式定义和排除各类边缘群体,实施一种符号的权力,而且利用学校、监狱等场所对个人进行规训,以实现指称的定型。总之,按照这一思路,身份政治在消解以二元关系为基本特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构传统意义上“他者”体系,抵制资本主义对生活世界的侵蚀,释放其批判性。
身份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了一种“暧昧不清”的理论关系。首先,身份政治学的政治光谱非常复杂,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抑或是中间力量都参与其中,但其中左翼是主导力量。身份政治学是在左翼力量的主导下,回应各个身份群体的自我重塑和寻求相应权利的政治诉求,以实现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重新唤醒革命意识的政治策略。历史地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右翼把控的极端民族主义身份认同政治已被迫退居幕后,那些依附在传统框架内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身份问题逐渐边缘化,此次是左派而非右派在推动身份政治[10]。因而,虽然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但左翼知识分子在转向并主导身份政治后获得了继续抵抗的政治力量。对此,伊格尔顿的评价非常精准,他认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已经不再时兴,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重要地位。而被称为‘身份政治’ 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传承着左翼的传统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并且,从长远意义看,这种运动可能会成为广泛的民众运动”[11]。其次,身份政治学深刻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传统,尤其是体现了超越社会既定现实的理论姿态,却又不同程度地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忽视生产力归根到底的作用,极力淡化阶级色彩而突出文化意识形态。[12]许多学者宣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开拓,是对“经济决定论”“阶级还原论”的超越。且不论是否真的实现了超越,显而易见的是,某些思想已经溢出马克思主义。因此,尽管身份政治学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却无法被视作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运动。
许多左翼思想家——包括“英国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后殖民理论“圣三位一体”之一的霍米·巴巴、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发言人霍耐特和南希·弗雷泽在内都卷入了围绕身份政治学所引发的当代社会批判的讨论之中。总而言之,身份“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一致的主体”[13],以一种不稳定的方式在性别理论以及后殖民理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逐渐在社会学、文学以及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中言说。
多元文化主义式身份政治
想象差异中的同一新世纪前后,以特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抗支配性旧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多元文化主义式身份政治和以承认理论为问题导向的正义式身份政治的两大典型理论模式共同促成了西方身份政治共识的最终形成,身份政治学进入鼎盛时期。多元文化主义式身份政治是女性、黑人、移民等社会边缘化群体为保护和提高群体利益而开展的一系列综合性社会策略。尽管已经构建起一种公民政治身份,在现实中仍然无法避免由性别、肤色、族裔等差异所引发的不公正对待,这是一种来自主流的压迫性同一性逻辑的力量,它拒斥差异性身份。无论是斯图亚特·霍尔自20世纪60年代带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启种族研究后逐步转向了身份政治,还是霍米·巴巴经由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的中介后形成的身份政治立场,目的都是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神话的批判和解构。
持这一立场的学者普遍认为,身份/认同不是对某一本质化的主体位置的恢复,而是在现实社会中进行定位的过程。差异是定义身份的关键概念,它具有双重内涵:一种是集体的符码;一种是更为具象的特殊性。前者指的是拥有共同历史经验、共享同一套文化符码的人们所共有的“大写自我”,给人们提供的是“实际历史变化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相对稳定的、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14]。它恢复了那些原本被遮蔽起来的、无法言说的身份,用想象的一致性重建和再现了过往碎片式的经验,因而是所有其他更具体的差异的基础,在后殖民斗争、反种族主义以及女性主义运动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关键作用。后者则强调差异的断裂处和非连续性,即构成某一身份的独特性,指的是从同一、固定的个体主体向动态的、交互的多元化主体的转移,决定了身份应该是被建构之物,而非固定之物。换句话说,此时的差异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正如霍尔总结的:身份认同与其说关注的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之类的问题,不如说更重视的是“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如何表现自身”等问题[15]。身份政治的认同时刻就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定位,是关于位置的政治学”[16]。
与此同时,他们又并非把差异绝对化,而是强调“差异中的同一性”[17]。任何想要实现在当前社会过上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共同社会的想法,就必须找到一个“可协商的共同点——在不抛弃差异性,即那些塑造我们身份的差异性的前提下,寻求共识”[18]。差异性永远不会消失,不会自动隐匿,这个社会本就是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与历史经验的人构成的。只有把握好差异性与同一性之间的张力——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以压制对方为目的,既不能依赖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也无法轻易信任西方所提供的普世价值的工具箱,差异性之间的缝合即使必须在共同的框架内部才可能进行。
具体到现实社会中,传统意义之上的工人阶级已经分化为多元的政治利益集团,他们围绕一整套不同形式的社会差异,并为了相应的身份利益诉求而积极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式身份政治正是把这些差异从附属于阶级的角色中抽离出来,通过“自己的语言言说自身,并塑造自己的身份,为了相应的权利诉求而斗争”[19]。他们的现实诉求既包括物质利益、权利保障等经济政治诉求,又强调社会对新兴生活方式的尊重等类似的道德诉求,以达成政策倾斜和文化认同的核心目的。但这是一种并不直接指向国家权力,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以游行示威等非暴力革命形式下追求的一种社会自治。
正义式身份政治:再分配与
承认的双重维度尽管正义式身份政治在重新定义身份以及相应的现实策略问题上,与多元文化主义式身份政治存有基本的共识,但细节上表现出更多的分歧。正义式身份政治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逻辑转向承认问题的延续,尤其是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发展。它是为澄清当前流行的“反常规正义”问题而尝试进行的一次政治理论建构,凭借社会正义批判理论的新范式,以此分析由身份关系引发的“后社会主义冲突”[20]。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前辈的方式并不能提出有益于资本主义现实改良的方案,因而集中于建构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从而开启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批判到政治伦理的理论逻辑转向。学派的第三代发言人霍耐特、弗雷泽在批判和吸收哈氏的理论过程中,又与资本主义现实的当代变化相结合正式踏入以承认问题为中心的正义式身份政治探讨领域之中。
在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正义式身份政治内部经历了一次从前者取代后者到两者互为补充的争论。诸如霍耐特这样的学者已经完成了彻底的“承认理论”转向,认为“再分配”与“承认”两者相比,后者更为基础,并且身份政治应取代阶级政治成为当前社会的主导形式。其依据是“分配正义归根到底是一种通过资源的再分配,使所有主体的权利得到规范性承认的正义理论,当前的分配不公正本质上是不对等的承认关系的制度性表达”[21]。但弗雷泽认为,这是一种试图以“承认逻辑”替代马克思的“劳动逻辑”来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做法,已然把“认同”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用“承认斗争”取代“阶级、经济斗争”,完全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对此,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社会正义兼具经济和文化双重维度,不可化约,因而身份政治不是对阶级政治的取代,而是对世纪末社会正义新诉求——“认同”的部分回应,提出了“再分配/承认的二维正义”理论。其不仅指认霍耐特的思路仍然是一种还原论——用“文化”替换“经济”,而且强调尽管当代社会涌现出了大量的多元价值观念和新兴的生活样式,依靠分配性的单维正义理念已经无法作出有效的解释说明,但这并不代表经济上的不平等已经消失或再分配问题已经得以解决。相反,“后社会主义时期,不但分配不公正没有消失,经济不平等还在疯狂增长,因为新自由主义力量削弱了从前的某些再分配的治理体系”[22]。即是说,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是遭受双重社会差异压迫的群体,既在经济层面被剥夺,又在文化层面被污蔑。所以,单一的阶级政治或者单一的身份政治都是不充分的,只有将再分配和承认视为正义的两个维度,才可能实现更全面的美好社会生活的理想追求。
正义式身份政治认为只有把“身份”概念重新概念化为“地位”,解构差异,才能走出原有“身份模式”的困境。原有的身份模式助长了群体隔离的意识,尤其是右翼身份政治的卷土重来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其结果不是推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认同,而是煽动了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而在现实运动中追求特殊身份认同演变成为一种畸形的“政治正确”,一定程度上将身份固定化、本质化。基于此,弗雷泽引入“参与平等”概念,制定出正义式身份政治的新方案——主张变革的非认同主义政治。它具体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公民资格问题,即人们作为平等主体参与社会活动以及提出正义诉求的资格;二是正义构建的程序问题,即决策从提议到实施的实际全过程的规范性。这种“地位模式”通过解构人们的身份差异,从而确保全体成员在再分配过程中的平等机会,以及明确其获得社会认同的公平机会。但是,这种“承认的反本质主义文化政治与再分配的平等主义社会政治”[23]的结合方案的可行性依旧值得质疑,正义式身份政治的支持者们只是给出了理论上的可能性,而非现实的可操作性。
身份政治学与新自由主义
对抗,还是共谋身份政治学的兴衰与新自由主义的展开密切相连,新自由主义既提供了身份政治学等一系列左翼社会思潮兴起的现实基础,又在过程中收编这些反资本主义力量。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演进期(20世纪70年代—21世纪初)可视作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又一次狂欢盛宴,他们通过推动全球化,凭借历史积累形成的优势,获得超额利益。一方面凭借其在全球竞争体系中的优势地位,通过利用“跨国资本”[24]在发展中国家的跨时空流动而攫取巨额利润,为身份政治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则通过内部和解、共谋、共享超额利益,发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促使身份政治共识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改良“工程”的一部分。
从总体上看,身份政治学的理论变化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①高度重合。20世纪60、70年代,当时的社会仍然处在凯恩斯-福特主义之下,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的催化下,新自由主义已经萌芽,这一时期的政治话语也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阶级”被抽离;二是“资本主义制度问题”被搁置。前者有利于激进社会运动以“身份”——女性、种族和性别等形式出现,成为身份政治兴起的初始背景。后者资本主义的社会逻辑则利用福利社会的“温床”使人们产生了“问题并非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错觉。这一氛围下的身份政治或许可以针对表层的社会不平等关系,却注定不可能深入到最根本的社会关系之中。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英美两国逐步确立,并迅速在全球扩散。虽然失业率相比战后初期仍然较高,但结构性危机已经解除,经济势头良好。身份政治学在该阶段进一步发展,甚至创造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神话”。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乐意支持某些反歧视政策,前提条件当然是不触及少数精英的利益。因而,虽然身份政治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多数政治活动却是从“超越新自由主义(over neoliberalism)”的目标转变成“为了新自由主义(for neoliberalism)”[25]。当全球化成为21世纪初最重要的“结构性动力”之时,它就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也与个人和群体的变迁密切相关[26]。21世纪初,金融危机爆发,经济衰退,失业骤增。一方面为了转移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视线,另一方面事实上整个欧美社会已无力再继续回应左翼身份政治的诉求,身份政治学顺势成为最明显的危机表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操作是将矛头指向身份政治,而非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尽管身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相互缠绕着一道跌下神坛,但只有前者几乎被摔得粉碎。
身份政治学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社会实践之中对改善新自由主义展开过程中加深的各种不平等关系发挥了毋庸置疑的作用。在理论层面,身份政治共识深化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解构了“欧洲中心论”。基于白人男性基督教文明的价值体系的欧洲中心主义,不仅仍然渗透于民族解放运动后的第三世界的方方面面,而且在西方国家内部也占据主导地位。它在当代还常常变换新的面貌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运作。身份政治学以性别主义批判、后殖民主义批判等微观局部话语反抗等级的权力压制,揭露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重新书写全球化时代的“女性”“东方”“黑人”地位。实践方面,则为边缘少数群体赢得了一定的社会权益,缓解了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针对教育、就业等领域中存在着歧视和偏见,制定和实施相关倾斜政策;另一方面宽容的社会气氛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力的条件,从而提升了全体公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对整个资本主义来说,身份政治学在批判过程之中逐渐被吸收、收编,成为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助手。
身份政治学是经由“市场化”成为新自由主义政治工程的其中一环的,其否定性的批判力量逐渐减弱。新自由主义强化了商品化的市场主导逻辑,任何人作出的表面上个性鲜明、差异化选择都被抽象化为同一“消费者”身份下发生的交换行为而已。“那些我们熟知的医疗关系、师生关系、国民关系等当然有着具体的、多样的社会内容。一旦我们被说服,把我们自己视为消费者之后,所有具体的社会关系就立刻还原到一个共同的分母,即我们在只能通过付费产生价值的市场中进行消费这一事实。”[27]资本主义商品逻辑之下身份政治学不仅帮助企业塑造各自的品牌,而且为市场提供现成的目标客户群。它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下向私人领域回归,成为多样性掩盖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以及同一性再生产的话语机制。
这一切正如哈维所言:“任何将个人自由提升到神圣位置的政治运动都有被新自由主义收编的危险。新自由主义修辞以期对个性自由的基本强调,有力地将自由至上主义、身份政治、多元主义、自恋的消费主义从想靠夺取国家权力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28]如果身份政治学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当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来临,身份政治学必然将遭受严重挑战。
身份政治共识的断裂
身份政治学自兴起开始就有批判之声,只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质疑呈井喷之势。其中有两种声音最具代表性:一是指认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逻辑再生产的意识形态机制;二是批判身份概念的内在排斥性,指责其无法构建起总体性的政治联盟。
早在20世纪末身份政治学正如火如荼之时,齐泽克就从拉康精神分析视角审视当代左翼政治行动,认为其本质上是一种虚伪的“受害者政治”,只是一次在大他者中介下完成的自我异化,而非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
第一,普遍的受害者逻辑阻碍了不同群体间的政治联合,陷入点式局部抵抗的困境,难以形成有效的总体性政治介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害者身份被重新界定,与性别、生态以及种族等特殊群体相关联,从而形成“后现代受害者学”。它强化了一种受害者意识,受害的意义从原初个人的具体例外经验扩展成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普遍性体验。“受害者身份”动员人们加入一种基于痛苦体验的政治行动之中[29]。对此,齐泽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受害者情结”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精英阶层的“自恋逻辑”,是“后政治(post politics)”[30]时代的一次“虚假行动”。当身份政治以“政治正确”的名义为少数族裔、性别群体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时,资本主义则继续迈着气势昂扬的步伐前进。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不可能是单个的文化差异群体,必须重返阶级,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干预才可能形成普遍化的斗争。身份政治学表面上看似极具反抗力量,实际是与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相匹配的意识形态框架。身份差异中的解放力量并不足以动摇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企图从这些被主流符号排斥的边缘群体中寻找真正的革命力量是无法实现的。无论是游行示威,还是静坐请愿,只是象征界中的一次“驯化”,资本主义反而通过一定限度的妥协和退让赢得了统治地位的巩固之效。因而,齐泽克提出重返阶级斗争(return ofclassstruggle)[31],展开激进政治行动。这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强调阶级视角,重塑无产阶级概念;二是将阶级斗争而非多元文化主义身份政治视为行动的关键策略。
但齐泽克的这次重返,与其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续,不如说是经由拉康精神分析中介意义上的解读。他把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拉康化,先是指出人们由于受到排除而无法在社会中获得合法的位置,而呈现为“非人”状态,被迫“无产阶级化”[32];而后指认阶级斗争是“一种创伤性限制”[33],并且“秘密地多元决定着真正的地平”[34]。多元文化的身份斗争要么搁置资本主义的制度问题,要么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局部抵抗,无法承担起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中心角色。不过,齐泽克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客观的现实存在,只是一种穿越幻象的“征兆”,局限在抽象的理论分析批判和激进的政治想象之中,不可能真正发起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另一种批评的声音来自普遍主义。普遍主义的价值重新被重视,正逐渐掀起一股新浪潮,试图推进一种跨越局部边界、追求共同利益的总体性政治理论。霍布斯鲍姆首先论证了身份政治的狭隘,表明身份政治学不能胜任左翼运动的基础。他给出了三点理由:一是左翼的政治图景应是面向全人类,而非女性、少数族裔这样的特殊身份群体,“身份政治本质上只是为了那些具有特定身份的成员”[35]。二是投入身份政治中的团体,更多的是为了身为其中一员可获得的利益。因而这些团体对左派所作出的承诺,是不可信的,无法通过共享的价值和目标形成可靠的联盟。三是过度运用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负面影响已经蔓延。尽管左派尝试通过支持更多的身份团体规划出一条更为广泛的政治联合之路,但霍布斯鲍姆尖锐地道出“少数相加并不等于赢得多数”[36]的现实。阿马蒂亚·森认为,无论是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还是身份政治学,本质上都是一种建立单一性身份认同基础之上的观点。特定身份认同带给人们归属感的同时,也加强身份固化并由此引发恶果,单一性身份幻象(illusion of unique identity)可能会引发社会暴力和冲突。在不平等关系强化下生产出的“应激性自我身份”很容易迷失在身份幻象之中,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下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盛行。奈格里和哈特把矛头对准后现代理论,宣告一切经过后现代主义浸染的理论的终结,直言身份政治已经成为“帝国”的助手。他们形象地指出,“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会走入死胡同,因为它们未能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说,它们认错了敌人”[37]。换句话说,“帝国”成为资本主义全新的统治形式,这意味着建立在身份政治学的对手,已经改变了统治策略。如果身份政治学还停留在“对旧权力形式的攻击中”,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将刀剑挥向了敌人的影子”[38],甚至身份政治学本身追求的差异和混合就是帝国的发展方向。新的政治秩序已经完全消解了身份政治学的否定性力量,成为“帝国”的“共谋者”。
为了卸下过去那些已凝固在人们身上的身份,这些学者提出了有关未来共同体的身份认同的几种设想——公民民族主义、全球团结以及新共产主义身份。霍布斯鲍姆号召左派应竭尽全力遏制普遍主义的衰落,想办法建立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全面的身份政治,即“公民民族主义(citizen nationalism)”——国家身份认同。虽然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这一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与普遍主义相对立,但由于民族-国家架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不会发生改变,因而这一方案将继续为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共享价值。尽管这其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在全球化不可逆的现实情况下如何避免走向“极端民族主义”,它就还无法作出明确的解答。阿马蒂亚·森的方案则是强调身份的普遍多重性,认为不应该用某一种宗教、国籍或者种族对人类进行划分,从而提出建构一个理性和自由优先的“全球团结”[39]之可能世界。在他看来,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差异,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保证身份的多样性实际上是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奈格里和哈特采取的方式或许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他们提出了“共有社会”这一资本主义替代方案,通过竭力塑造对未来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以构想一种“新共产主义”身份。同样清楚的是,这与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并非是一回事儿。与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认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经无法担任反抗“帝国”的重任了,新全球政治秩序之下的革命的主体力量将是从帝国内部生长出来的“诸众(multitude)”。他们宣称,“人民”和“群众”都是消除差异的整体性的概念。与此相对的“诸众”则是“所有个体差异的多样性集合”[40],既保留了传统工人阶级的位置,又将黑人、女性以及同性恋者这样的边缘群体容纳进去。即是说,“诸众”是所有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人的普遍联合。然而,“诸众”虽然被视作是无产阶级概念的更新,但现实证明诸众并不能作为革命的真正主体,而只是理论分析的对象。
身份问题的本质是资本主义框架下,经济、政治不平等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表达,只有扬弃资本主义,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身份政治学在反对经济决定论和阶级简化论的过程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经济问题在归根到底层面上的作用,没有触及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过度强调文化维度。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借鉴了马克思的理论思路,甚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接受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因此,金融危机爆发后,身份政治学并没有在新的机遇之下取得新的发展,反而遭受重创,与此相对的是有关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等马克思的经典议题重归视线。这说明,新的社会变革不会出现在资本主义改良方案的身份政治学之下,最终仍然要回到直面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之中。
注释:
① 1947年至1973年期间,年均失业率4.8%;1974年至1979年期间,年均失业率6.8%;1980年至2007年,年均失业率6.1%。金融危机发生后(2008—2013),各年的失业率从未低于7%,最高达到10.1%。(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3)
参考文献:
[1][35][36]Eric Hobsbawm.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Left. New Left Review,1996, 217.
[2]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B Tauris, 2013:445.
[3]R.H.S.Crossman. Socialism and the New Despotism. London:Fabian Tract,1956:3.
[4]Vlad Mykhnenko, K. Birch.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ism: The Collapse of an Economic Order?. London: Zed Books,2010:23-41.
[5][28]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3、41.
[6]Jürgen Habermas. What does Socialism Mean Today? The Rectifying Revolution and the Need for New Thinking on the Left. New Left Review, 1990, 183.
[7]Colin Barker. Marx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3:259.
[8]Andre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lack Rose Books Ltd., 1980:20.
[9]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1997:56.
[10][29]Frank Furedi. The Hidden History of Identity Politics. Spiked Review,2017, November.
[11] 伊格尔顿,王杰、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文艺研究,2008(12).
[12] 牛先锋、刘雅琪.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双重考量.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13]Richard Jenkins.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2004:8.
[14] [16]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The Journal of Cinema and Media, 1989(36).
[15]Stuart Hall、Paul Du Gay.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Sage, 1996:3.
[17]Stuart Hall.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 Pavis Paper,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Milton Keynes: The Open University, 2000(5).
[18]Stuart Hall. Living with Difference. Soundings, 2007(37): 148.
[19]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2003:214-215.
[20] 南希·弗雷泽, 于海清译.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