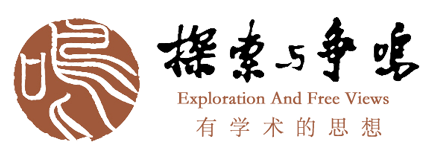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杜春林
内容摘要 以行政发包所包含的财权与事权为切入点,可以观察政权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据此构建行政发包制与政权兴衰的分析框架;并探明西汉政权发展的主要历史事件与行政发包制理论之间的契合之处,以阐释西汉政权发展的脉络与兴衰历程。从中,中国历代治乱循环的一般逻辑也得以显现:2000多年的行政发包历程实际上是行政发包制不断完善的过程,行政发包制中所包含的集权与分权的概念就像钟摆一样在不停的摇晃,但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小——这表明行政发包制所隐含的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平衡。信息技术、民主化的发展以及央地之间权力分配的日趋合理,使行政发包制对现代社会政权兴衰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于行政发包所关注的焦点,可能更多地偏向社会服务而非权力划分。
关键词 行政发包制 分权 治理效率 政权兴衰 西汉
近年来,行政发包制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现有的研究中笔者归纳了这样几点认识:一是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行政发包制是介于雇佣制和发包制之间的一种制度安排。[1]二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看,强调行政发包制是属于纯粹的科层制和外包制之间的混合形态。[2]三是从控制权理论的角度来看,行政发包制是中国政府常态的治理模式,委托方设定目标和政策取向,然后将任务“发包”给下属管理方,并在管辖范围行使自己的剩余控制权来安排落实政策执行活动。[3]不可否认,行政发包制的确是作为当前国家治理理论的现实存在,而且还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问题,对行政发包制的进一步研究,促使笔者追问行政发包制所发之
“包”谓何物?为什么将这些权力发包给地方政府就会存在治理效率以及统治风险等问题呢?本文拟在这些追问的基础上,分析行政发包制与政权兴衰(即治理效率与统治风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行政发包制与政权兴衰
——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中央向地方所发之包主要是财权与事权的执行权和决策权,自上而下的财权是行使事权的物质保障。在中央政府的行政发包过程中,财权始终处于最活跃的位置,财权的分配是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重要手段,而由于受中央政府获取信息能力的束缚,再加上地方政府与事权的决策和执行紧密相连的特征,使事权始终停留在地方,中央政府对于事权的发包仅仅是体现在政策文本上,对于财权的发包才是最具影响力的。而在政权发展的每个阶段,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分配都存在一定差别。在政权初建时,中央政府倾向于高度集权,行政发包相对谨慎,分权所达到的治理效率提升效应也不断扩大,政权也随之兴起。政权兴起的过程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发包由集权向分权发展的过程,但始终偏向于集权。经过政权初期兴起的积累,中央财力充沛,财权进一步发包,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日益匹配,由此也形成一个政权最兴盛的阶段。当然,由于事权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始终在地方政府,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事权的行使必定包含财权的下放,在政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会形成持续的行政发包,地方政府也会因此逐渐财大气粗,“占山为王”,垄断财权与事权,形成诸侯割据。另外,晋升的“天花板效应”,使得行政发包制下的激励机制失去应有的效果,从而对中央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过度的分权(行政发包)会导致治理效率的下降,进而导致政权衰落甚至更迭。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政权,大致都会经历兴起、兴盛和衰亡三个阶段,可见时间因素在政权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图1所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政权建立初期,中央政府能利用财权有效地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和激励地方政府完成属地管理,提高治理效率(AB)、降低统治风险(DE)。而在政权中后期,中央政府财权的控制作用逐渐降低,以至于形成地方诸侯经济,甚至藩镇割据现象,导致治理效率下降(BC)、统治风险提升(EF)。从图中还可以看出,行政发包也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反映了中央政府在发包过程中集权与分权的差异,也决定了政权是否向稳定的态势发展。因此,本文拟选择西汉政权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行政发包制与政权兴衰的内在逻辑。西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发展脉络相对清晰的政权,经历汉初的休养生息以及“文景之治”而兴起,到汉武帝时的兴盛,再到西汉后期的外戚专权由盛转衰。另外,西汉政权的建立也初步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发包关系,行政发包制理论能够合理地解释西汉的央地关系。
行政发包制与政权兴衰的内在逻辑
周黎安从宏观上阐述了中国古代的财政体制具有包干制的特征[4],但是对于包干制在一个政权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特征并没有给予过多的解释。本文拟在其研究基础上,利用行政发包制理论揭示政权兴衰的内在规律。
(一)谨慎发包与政权兴起
从事权和财权的划分来看,行政发包与统治风险之间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事权的分配与统治风险之间的关系,央地之间的财权分配也与之相似。这就可以解释政权初建时,中央政府更倾向于集权,自上而下的放权总是谨慎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权的统治风险,为政权的巩固、兴起奠定了基础。换言之,行政发包过程中的谨慎态度,为汉朝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行政发包制所包含的集权与分权逻辑中,政权初建时各项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但由于百废待兴,中央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治理效率的问题,必须要将相应的财权与事权下放到地方。由于实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政治体制,封国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军权与财权。在汉景帝平息“吴楚七国之乱”之前,西汉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央-郡、国-县三级的财政管理体系。[5]从汉初的实际情况来看,汉高祖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削弱异姓诸侯王的初衷是加强中央集权,避免秦末的诸侯四起、群雄逐鹿。对此,王国维清晰地描述了汉高祖刘邦大封宗室子弟、恢复血缘关系、建立宗藩制度的概况。[6]在高祖刘邦看来,建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藩制度胜过秦代的郡县制,有助于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司马迁与班固对于分封同姓诸侯王也有过较多的论述[7]:
“故王者疆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史记》卷60《三王世家》)“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汉书》卷14《诸侯王表序》)分封同姓诸侯王反映了中央政府对于代理人的甄选,与异姓诸侯王相比,皇帝对于宗室子弟的了解程度更高,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进行行政发包更有助于中央对属地管理,有效地接手和贯彻中央所发之“包”。政权初期的集权重塑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有效的行政发包奠定了组织基础。
2.上计制度与财权一统
秦汉建立之初就沿用战国时期形成的“上计”制度,来加强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状况。县令常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状况等编制为计簿,呈送郡国。根据属县的计簿,郡守国相再编制郡的计簿,上报朝廷,朝廷据此予以升、降、赏、罚。西汉政权刚建立,刘邦就致力于恢复上计制度,任命秦代主管上计官吏张苍为计相,主持全国上计工作,西汉的上计制度无论在机构的设置、官吏专职化以及上计内容的广泛性方面,都远比秦代完备、合理和规范。在汉初郡国并行的中央-郡、国-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下,尽管封国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权,但是依然受到上计制度的约束。每年岁末,县、道必须上计于所属郡、国,再由郡、国上计于中央,汉代据此分两个层次进行上计。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发包的方式将事权与财权层层发包,实现属地化管理,但又通过严格的上计制度约束达到层级节制、有效控制的效果。中央通过上计制度对地方财政进行摸底,有助于中央财政政策的最终制定。上计制度保证了中央政府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在以农业立国的西汉财政收入主要以粮食为主,上计制度不仅保证了田租、赋税收入,还保证了兵役、徭役等顺利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央对地方实际情况的了解、监督和控制,也反映了在政权初建时期中央政府谨慎发包的心理。
3.紧缩型财政政策与开支的压缩
汉初中央政府谨慎发包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采用无为而治的紧缩型财政政策,在上计制度直接控制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前提下,紧缩的财政政策得以有效的贯彻,主要表现在尽可能地压缩地方建设规模,以此来限制地方政府的行为。汉初虽然沿袭秦代的旧制,但由于政权处于战后重建的困难时期,因此加强对财政的有效管理,坚持“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理财理念,对于巩固政权和振兴经济尤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看,汉初的休养声息政策即紧缩的财政政策,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其主要表现就是想方设法增加收入,尽量缩减政府开支、压缩建设规模;同时配合其他经济手段,比如货币政策、漕运政策等,以抑制不稳定发展因素,进而减少赤字或增加盈余。关于控制地方政府支出,以地方水利工程建设为例,马大英认为,地方水利工程费用可能由地方政府负担,但较大项目多须呈准中央后才动工。[8]不仅如此,汉初的财政分配原则,可以说是“量米过日子”,为了保证国家预算的实现,国家同时加强财政管理,处罚不称职官员。[9]应当承认,汉初紧缩型财政政策,作为西汉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强有力工具,在最初一段时间的确起到一定的历史“杠杆作用”。[10]正是由于紧缩型的财政政策与谨慎的行政发包相结合,保证了中央集权财政体制下的财政收入,也为行政发包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适度发包与政权兴盛
在专制制度下,皇帝对官吏的控制最主要的是掌握各级官吏的任免权。[11]因此在盛世,无论地方政府如何暗流涌动,都不可能对政权造成致命的威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有力地掌握了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对不遵循中央政策旨意的地方官员可以随时进行罢黜。中央政府无限的干预权,实际上就是用来灵活应对地方政府日益膨胀的自由裁量权。
1.扩大行政发包的基础
西汉自建立之后,中央政府在行政发包制所带来的巨大的地方治理效率的推动下,不断扩大发包力度,促进地方发展;与此同时,也强调对政治权力的集中,包括人事任免权、干预权以及监督权等。汉武帝掌权后,主要从两个方面扩大行政发包的基础。一方面,他在政治上的举措主要有三:颁布推恩令、建立刺史制度和重用酷吏。首先,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扩大行政发包的组织基础。其次,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开始在全国推行刺史制度,作为汉代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所实行的一种较为完备、系统的监察制度,对各郡国起到重要的约束作用。最后是重用酷吏,西汉的酷吏共计18位,而汉武帝一朝就有10位,且均威名显赫,酷吏不仅能加强中央集权,还能起到威慑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中央财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王家范认为,集权与分权乃是一切国家权利统治必难避开的两极,仅执其一端,必偏执僵硬而丧失生机活力。[12]财权分配方面更是如此,中央政府在确保资源独占地位的前提下,又不得不给予地方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以保证整个国家财政机制的有序运转。汉武帝时期通过多项手段加强中央财权,中央政府在财权的分配上占有绝对的主动权,也即国家具有很强的汲取能力和调控能力。因此,这一时期中央政府“财大气粗”,依靠庞大的财力和强有力的政治控制,保证了行政发包制过程中分权的效率与社会的稳定。
2.地方自主性与地方建设
行政发包制的治理效率发挥需要向地方分权,给予地方政府自主性。中央政府持续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权与事权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从政权初期谨慎发包中尝到了分权的“甜头”,就拿西汉来看,“文景之治”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一时期国库充裕,地方治理也井井有条,因此进一步分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具有巨大的诱惑。但是,如前文所述,事权始终具有下沉的倾向,尤其是事权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始终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来实施。不仅如此,随着政权的发展,地方政府所管辖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客观上要求中央政府加大发包力度和范围。因此,分权并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性,成为行政发包制随着政权稳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地方政府自主性,反而会提高治理效率、降低统治风险。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对于其发挥地方治理的作用不可小觑,这也可以解释一个政权的大规模建设之所以都出现在政权兴盛的时期,不仅仅是因为稳定的政治环境、持续的财政供给,还包括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汉代中央与地方之间配合得井然有序,在中央集中了财政税收、支配、监管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充足的自主性。[13]另外,汉代各郡有自己的公田,收入由太守支配,可以自主兴建一些诸如道桥、亭传、官舍以及小型水利灌溉等公共工程。西汉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达到了集权与分权的平衡以及适度发包,并带来治理效率最大化与统治风险最小化的状态,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盛世,直至西汉政权走向衰落。
3.激励机制与社会发展
纵向行政发包和横向晋升竞争的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去描述政府各项公共事务的治理特征和效果:在多个承包人面对一个共同发包人(发包人可以决定承包人的未来地位和报酬)的情形下,横向晋升竞争通过奖惩规则和相对绩效评估,为承包人提供了强大的争胜激励。另外,结果导向的考核和问责也让承包人为实现目标而“不择手段”。古代地方官员的激励与当前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如出一辙,依据的均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对于地方官员的激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在上计制度基础上的官员考核机制;二是对刺史的激励。中央通过上计簿实现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监督。上计簿是地方郡守政绩优劣的一面镜子,许多政绩卓著的郡守最终多位及三公。如汉代中期的丞相黄霸在任颍川太守时,“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14]。这也反映了在行政发包制下,地方官员的激励是建立在上计制度基础上、以结果为导向的体系,西汉地方官员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地方官员之间形成“晋升锦标赛”,激励地方官员励精图治,为西汉的繁荣与地方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此外,西汉的刺史制度是对以前监察制度的发展,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地方监察制度。刺史的俸禄很低,只有六百石,这往往能够促使他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待遇而加紧监察、取得业绩,比用更高的官员去监察地方大员更能起到好的效果,因此刺史往往很有政治前途,“居部九岁,举为守相”。这也保证了汉代中期地方官场的清廉与地方治理的良性发展。而汉代中后期刺史的地方官化与地方官员的腐败现象之间的关系,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西汉中期刺史制度的积极作用。
(三)发包失败与政权衰落
发包失败是指财权与事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非均衡分配,中央政府很难利用行政发包的方式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地方的有效治理,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中央政府过度放权导致地方政府财大气粗,诸侯四起以及各自为政;二是中央政府过度集权导致地方政府积贫积弱,社会动荡。不管哪种形式的发包失败都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因此,发包失败也成为政权走向衰落甚至覆灭的表征。西汉在经历长时间的发展后,地方政府逐渐做大做强,成为当地的主要管理者,尤其是富庶的地方政府更是富甲一方,在经济等领域与中央往往形成对立的态势,于文景之治和武帝盛世之后便开始逐步走向衰落。
1.事权垄断与地方官员权力膨胀
如前所述,事权的决策权和执行权主要在地方政府,尤其是执行权始终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这就难免导致地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张静认为中央政府通过默许的方法给予承包方“自由裁量权”,意味着它保留着“随时回收默许”的可能。[15]通过不确定性形成的行政威慑,上级对下级的过度控制可能构成制衡,可以抵抗走得太远的承包方。但是它又默许了地方政府的无限自由裁量权,在央地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不断膨胀,直接动摇了中央政府的统治,由此导致统治风险的危机。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之后,诸王的势力逐渐削弱,而太守的权力却不断扩大,太守集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于一身,在地方上独揽大权。严耕望认为太守统揽地方一切事务,当然,他也认为太守权力的膨胀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16]日本学者纸屋正和认为,汉武帝以后郡国的守相开始强化控制权,并由此逐渐占据了地方行政的中心位置。[17]在周长山看来“,从景帝时代开始,西汉地方政治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那就是郡国长官开始积极干预地方民政,甚至侵夺县道令长之职权”[18]。西汉实行中央集权下的分散管理体制,就意味着郡国首脑太守的权力空间很大“,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汉书》卷86《王嘉传》)。太守权力之大,在于其总理一切地方事务,垄断地方的事权,出现“倒逼”现象,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无法解除下级组织的代理角色,也不得不承认下级有自己的决策地位,委托方更无法选择另一个组织实施治理,这也是行政委托代理和市场委托代理的不同之处。[19]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被行政发包制所“套牢”。
2.事权沉淀与财权持续下沉
与科层制足额拨款的预算体制以及低自由裁量权相比,行政发包制可以说是差额拨款(甚至不拨款)和高度自由裁量权相结合的体制。[20]事权沉淀效应是行政发包制体制下政权发展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垄断事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事权的沉淀要求财权的进一步下沉,财权的下沉是中央政府增加发包力度的表现,可能面临所谓的“统治风险”,而中央政府只能在现有的格局下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事实上,从事权不断沉淀的结果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央政府总体上会对地方政府让步,也即财权会进一步下移,太守的权力不断扩张就是主要表现之一。前文所提西汉中后期的太守黄霸,后升至丞相,他在任太守期间所拥有的财权就反映了地方政府不仅财政自由度很大,而且在很多方面可以自行制定财政规则甄选官员。“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辛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呈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汉书》卷89《循吏·黄霸传》)事实上,这种财权的下沉并非因为地方官员个人的原因,更多的要寻找行政发包制的制度困境。从周雪光关于权威体制与统治风险之间关系的论述,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事权与财权的不断下沉,使地方政府通过各项“条教”的制定与执行加强了对辖区的控制,尤其是对下级政府财政的控制使中央政府处于被动地位,甚至架空中央政府。可以说,行政发包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经到了放任的地步,中央政府在财权上的被动地位进一步强化了统治风险。
3.权力中心的转移与政权衰亡
地方政府垄断了一个区域内的财权和事权后便逐步形成“沉淀效应”,使中央政府日渐陷于被动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权力中心的转移表现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的变通甚至是扭曲。我们通常所提到的“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并不是当今时代背景下所特有的现象,可以认为这一现象是行政发包制下所特有的。郭浩就指出,西汉修治“道路及邮亭”是地方政府的一项“面子工程”,有助于提升“外人”对该郡的“第一印象”[21]。在行政发包制下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但当事权与财权下沉时,地方政府更可以自主地决策地方事务甚至为所欲为。其二,西汉刺史由监察官向地方官转变的历程,正是事权下沉以及行政权力中心向下转移的一个重要表现。西汉末年,刺史在行使监察权的过程中逐渐向地方官转化,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汉武帝建立刺史制度的本意是加强中央集权,但随着刺史地方官化,并与地方官员沆瀣一气,反而增加了统治危机,形成地方分利集团,成为地方权力的中心,甚至常常对抗中央权威。其三,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风行,官僚为贪财趋利,凭借政治权力和雄厚的资本大肆兼并土地,虽然其主要兼并势力仍是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和大商人,但是这三者已经形成三位一体的密切结合,实际上构成当时西汉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22]土地的大规模兼并与集中,再加上地方官僚欺上瞒下、侵占土地、与民争利,财政权力逐渐向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官僚贵族集中,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还加剧了社会矛盾,直接导致政权的更迭。
行政发包制下治乱循环的一般逻辑与当代转型
本文运用行政发包制理论更多的是揭示政权发展的必然性及其规律,为理解行政发包制下政权的发展提供一个视角。从行政发包制对西汉政权兴衰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代治乱循环的一般逻辑。事实上,2000多年的行政发包历程也是行政发包制不断完善的过程,行政发包制中所包含的集权与分权的概念,实际上就像钟摆一样在不停的摇晃,但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小,表明行政发包制所隐含的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走向平衡。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我们也可以用行政发包制理论去发现并解释一些问题和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高度集权,无论财权亦或事权都集中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包力度与范围极其狭小,地方政府只能按部就班,很难发挥自主性。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中央政府通过适度发包,赋予地方政府自主性,使地方建设大规模展开,国民经济也迅速发展。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地方政府在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可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而对于地方政府是否会脱离中央政府的管控,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的时代,地方政府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但在信息化时代,中央政府更能实现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一是中央政府能迅速掌握地方政府的行为,二是媒体的作用让地方政府行为无所遁形,三是民主化进程推动了社会民众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因此,当前行政发包制运行相对顺畅并得以延续。
可见,信息技术、民主化的发展和央地之间权力分配的日趋合理,使行政发包制对现代社会政权兴衰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于行政发包所关注的焦点,可能更多地偏向社会服务而非权力划分。
[本文获《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三等奖]
参考文献
[1][4]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98、196.
[2][20]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6).
[3]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5).
[5][10]项怀诚.中国财政通史·春秋战国、秦汉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250、120.
[6]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551-552.
[7]高晓荣.汉代宗藩问题研究.南开大学,2014:38.
[8]马大英.汉代财政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227、367.
[9]孙翊刚.中国财政问题源流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91.
[11]薛军力.从汉代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变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0(5).
[12]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2.
[13]李治安.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47.
[14][21]郭浩.汉代地方财政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36、210.
[15][19]张静.行政包干的组织基础.社会,2014(6).
[16]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4.
[17]纸屋正和.前汉时期县长吏任用形态的变迁.刘俊文.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505.
[18]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0.
[22]叶振鹏.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192-195.
编辑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