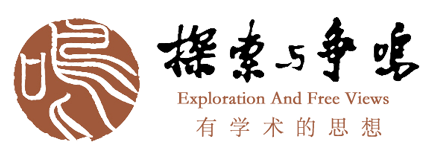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在波涛汹涌的中国改革时代, 当我们考察当代的信仰结构, 会发现所谓信仰的外衣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包裹着“私”的本质, 私人信仰陷入公共化困境且流于私密化认同。而且, 由于公私领域的相对隔绝, 一旦公共权力和宗教信仰趋于私密化的双向建构, 极可能衍生私化权力的绝对公共形式化和私密信仰的绝对公立机构化的双重异化, 进而全社会“获得性危机”显现, 即除了“金钱权力”的“拜物教”之外, 难以形成其他真实的信任。当一个由“自我主义”框架萌发, 更多地靠伦理来调节“公共性”与“私人性”, 文化、政治和经济形态呈三重原子化的社会, 迎面宗教改革500年后一个碎片化的、相对缺乏共识的时代, 其如何在古今中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错综纠结的格局中, 彻底走出私人信仰的陷阱?真正拥揽公共生活的关怀?为此,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特邀相关专家学者, 联合召开了“中国改革时代私人信仰的‘陷阱’”的圆桌会议, 希冀在公私关系的漩涡中, 重构私人信仰与公共生活的良性互动, 助力改革时代的中国改革!
专题主持人:李梅
改革时代私人信仰的私密化“陷阱”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讨论中国改革时代的私人信仰陷阱问题, 首先需要确定其时代背景。所谓改革时代的私人信仰陷阱, 应是指在改革时代呈现出来的状态, 但并不仅仅是改革时代塑造的结果。中国的私人信仰陷阱, 可以说其来有自, 源远流长。就这一论题而言, 可以离析出三个具体问题来理解。
中国改革时代私人信仰的私密化的几个概念界定
“中国改革时代私人信仰的私密化”论题包含几个概念界定问题, 自1990年代以来, 汉语学界的信仰含义非常宽泛但却没有明确解答。比如我们在这个概念下不讨论宗教的“神圣”含义, 而代之以讨论“神圣性”含义。前者是一个内涵清晰的概念, 唯有宗教才具有神圣的固定指向;后者则是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所有的世俗东西, 包括信念、迷信, 都有“神圣性”的含义。把世俗的“神圣性”含义提升为宗教的“神圣”指向, 是人们认识宗教与非宗教保有某种共同性的必须。但二者之间的确定界限不容混淆。宗教是在人与神之间呈现神圣状态的, 而非宗教则是在人与人之间展现某种神圣性的。在汉语语境中讨论神圣问题, 长期处于不清不楚的状态, 为了不至于将必要的界限抹掉, 有必要首先把信仰、信念和迷信的不同性质界定清楚, 不要把信念和迷信提升到神圣层面, 必须承认只有信仰才有神圣含义。信念与迷信的神圣性是世俗理念中包含的神圣性, 和宗教的神圣是两回事。与之相关的是区分宗教和宗教性两个概念。对中国来说, 本土没有成长起来的高级宗教都是外来的。且各种宗教的信众大多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现实精神寄托问题, 而不是虔信某种宗教教义。哪怕是今天兴盛的基督教家庭教会, 也不外如此。人们习惯于用某一个宗教来满足世俗生活缺失的精神寄托要求, 但他并不一定就是宗教信徒, 因为他并不把人归结于神, 让人性匍匐在神性之下, 他最多只能算是准宗教信徒。以此计算当代中国的宗教信众数目, 就有点为难了:官方认定的教徒仅有8千多万, 学者的推算大有不同, 从1个多亿到3个亿不等。从严格的角度讲, 这些信众的信仰之宗教性特点, 一般都超过了信仰的宗教特点。
有一个佛教的法师出了一本书, 坊间比较流行, 书名叫《宗教不宜混滥论》, 我很同意这一主张。国人可以什么都信, 改变崇信的宗教神格, 似乎也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在信佛教的时候拜佛, 信道教的时候拜老子, 到了孔庙他又拜孔子, 没有神圣归一的虔诚感。涉及改宗这么具有严峻挑战性的问题, 国人似乎也可以不当一回事。当年蒋介石为了娶到宋美龄就这么改宗了, 似乎并没有经历灵魂上的震荡。但在严格的宗教传统中, 改宗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 是灵魂深处的一场革命。可见, 即便是宗教信仰, 也得区分信徒虔信的对象固定性和神圣感, 不能以一种姑妄为之的随意态度审度。这就限制了人们将世俗性的准宗教信仰提升为宗教信仰的冲动, 也限制了人们将不同宗教信仰等量齐观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