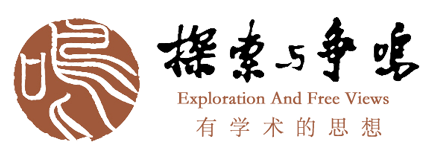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忆天佑
王家范
编者按 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回忆已故同事谢天佑的文章。
谢天佑(1932—1988),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研究班。历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职。他长期从事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思想敏锐、著述广泛,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与中国封建主义批判诸方面尤有建树。先后发表论文百余篇,并著有《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等专著。
作者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天佑在我踏进华东师大的次年,刚从“中国通史研究班”脱颖而出,留校进教研室。记得他在我们年级曾试教过二堂课,元明转折时段,讲课富有激情。1959-1960年发表《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若干基本问题的讨论》与《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两文,在五、六十年代的史学“五朵金花”中初露头角,显示“宏观理论”锋芒,步入新生代行列。党委副书记杨希康在全校大会上表彰他为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典范。另外两个样板,一是哲学系的丁祯彦,一是数学系的张奠宙。
1961年9月,我结束不断“运动”中的四年本科阶段,分配至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研室主任是束世澂先生,被指定为我的业务导师;谢天佑则已任政治副主任。天佑长我6岁,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没有架子,与他的亲近似乎是缘分,命中注定。我与天佑真正走近,还在4年后。跟着束先生学商周史(系里的培养规划),没“小学”文字底子,古文也读得不多,根本不是攻“商周”的料。好在老先生特别宽厚平恕,估计心里也有数,就随着我敷衍,从不加责备。
到1964年,天佑要我转到教学岗位上,辅助他上本科中国古代史课(每周4学时、二个学期),求之不得,而束先生也无二话,就此转轨,踏上“教师匠”一途。我慢慢把天佑的课接下来,到1968年“海罢”停课,已经整整教完了二个年级的课。天佑正在科研写文章的兴头上,放手让我去干。
我必须感谢这个安排,正是“中国通史”的教学,让我好好补了1957-1961“运动”式本科学习的缺项。我的中国古代史的底子完全靠边看书、边教书才补了回来,奠定了我后来写《中国历史通论》的基础。一直感激天佑对我的提携和帮助,方有今日。
直到1986年,天佑的研究重心都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其间,1978年11月23日-12月2日,由他发起召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是“拨乱反正”后,首次史界全国性的同仁学术集会。论战各方齐集,群贤毕至,22省市、140余人出席,可谓盛况空前(住第2、第3学生寝室,睡上下铺,吃河西学生食堂,真有“农代会”的模样)。
今天看来,它既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次历史性总结(详参《文汇报》“学林”版1979年1月19日、26日“会议学术综述”上下),又是“回光返照”最后一个高潮的先声。随后,学校批准成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室”,成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办事机构,天佑任主任,着手编辑会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共出四辑),为“后高潮”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学术纪录(直到1988年10月第5届年会上,由我赴山东济南,代表天佑在会上交盘)。
据夫人陈翠姬口述,天佑在1986年4月手订有自选集《泥径鸿爪——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收录代表性论文22篇,意欲甩手收摊,开张新业,惜乎未能梓行,就遽然离世。真被天佑不幸而言中,雪泥鸿爪,过后了无痕迹,出生晚的史学俊秀已经不容易体会这段时期求索背后的心境了。
在农战史研究50-60年代高潮与80年代“后高潮”之间,天佑的学术曾被中断十年。姚棍子用《海罢》兴风作浪,除有钦定的特殊政治目的以外,还负有横扫“反动学术权威”的“使命”。起初天佑仍被当作“自己人”,从朱永嘉那里领受“任务”,回系组建了“革命大批判组”,我是组员。
然而,没多久,朱永嘉发现天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原话),书生气十足,错以为还在搞“学术批判”,死抠史料,坚持用史实说话,不懂得“拎辫子”(王知常语,即上纲上线),从政治上置吴晗、翦伯赞等人于死地。大失所望后,索性把他凉在一边。待到师大红卫兵把天佑也划入“反动学术权威”范畴(时称“小牛鬼”),他个人的科研也被迫完全中断。
朱永嘉自诩“史派”,瞧不上“论派”,然而,罗思鼎十年里风起水涌,八面出击,深得上意,恰恰变成了面目可憎的“论派”,正宗史学被蹂躏到不可言状的地步。什么“史派”与“论派”?治史者内心善与恶,人品美与丑,才是天壤之别,荣辱皆由自取。
十年的经历,既是一场人生噩梦,也是灵魂得以洗刷、良知得以清醒的难得良机。天佑在1978-1988短短的最后十年里,身上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都与对这段时期的反思相关。陈旭麓先生留下《浮想录》,让我们得以了解先生一系列内心独白,而天佑没有。
记得“四人帮”被粉碎前,到市内看内部电影《山本五十六》。走出影院,天佑建议去徐家汇图书馆看望陈先生。我与陈先生此前几乎没有单独接触过,天佑常去二村见先生,无话不说,正如陈先生在《专制主义下的臣民心理》序言中所说的,“(他)从研究班毕业,留历史系任教,我们得以认识,以思虑接近,论学论事,常相过从,历三十年风雨不谕”。
那天,说起“四人帮”迫害周总理,陈先生非常愤慨,突然吟起鲁迅的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证明两位朋友间晤谈,百无禁忌,相互绝对信任,在那种年代里十分难能可贵。 虽然没有陈先生《浮想录》那样的手记,但天佑写下了不少自称“豆腐干”式的读史札记,倾泻所感所思,可稍补缺憾。
1979年开始,天佑突然文风大变,着实令朋友们惊诧莫明,原来天佑也是个久被八股论文“遮蔽”的散文家。心思很细,文字凝练,笔锋犀利,现实感很强,常带有往昔血污残痕,让人觉得苦涩。1979年开始,天佑突然文风大变,着实令朋友们惊诧莫明,原来天佑也是个久被八股论文“遮蔽”的散文家。心思很细,文字凝练,笔锋犀利,现实感很强,常带有往昔血污残痕,让人觉得苦涩。
那年他写了张汤密告颜异的《“腹诽罪”》:“司马迁对颜异之死很悲愤,他写道:‘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媚取容矣!’这‘以后’延续得多长,是司马迁怎么也想不到的。”(《民主与法制》1979年第3期)1980年6月为《文汇报》写了《康熙的苦衷》,文末感叹道:“假如那时皇位不是终身,并且准许年老退休,那么,康熙这位开明通达的老皇帝,可能也就没有那个苦衷了!”
11月,他又为《解放日报》写了《“鄙人不知忌讳”》,“像冯唐那样不知忌讳而被无辜杀害者又何其多呢?为什么造成这种状况呢?因为那个时代里,君主就是法,大于法,高于法??????那些不知忌讳的仁人志士,倘若将命运系于所谓‘人主圣明’上,终究是不牢靠的。以古鉴今,亦如是也”。我希望天佑的门生能够把老师的散文札记收集梓印。这是又一种风格的学术,读起来很爽,能吸引更广泛的年轻读者深入理解国史,读史以益智。
有原创性的学者,治学的理路不会一成不变,也不会凭空跳跃。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当年论战“在场者”悉数到位,完整温习了一遍50-60年代争论的各种焦点。会上,以“农民战争的性质与作用”为中心,群雄仍各持已见,互不相让,很少见有“自我检讨”,似乎也没有新的话题提出(当年的《学术综述》,我故意留了条小尾巴,恐怕没多少人注意)。
但从事后回看,恰恰“新的变化”正是在此时以及稍后便萌动起来。“春江水暖鸭先知”,以“旁观者”身份与会的陈旭麓先生(他与“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始终没有任何关联),最先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农战史研究应果断抛弃原有“死结”,重辟蹊径,深入到“社会-经济形态”方面追根究底,整合到中国历史“总体研究”之中,才能改变前此各自称雄、内战不息的“农战史状态”。
先生言教兼身教。会议结束,先交出一篇论文:《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刊载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1979年1月),农战史界感到耳目一新。先生文章揭示出人口增长与社会矛盾激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人口激增同地主阶级的加紧剥削和农民失去土地成正比;生产力水平低,人口激增与农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人口激增与农民起义的频繁及规模成正比。”这一论述的深刻意义,在于标志着研究重心的转换,以革命为叙述中心向以社会变迁(走向“现代”)为旨趣的研究范式的转换。
而后,先生对天佑、对我都口头上分别表达过这层意思,谆谆劝导我们“改弦易辙”,从“社会-经济史”着手寻求突破,探究古老中国为何难于“走出中世纪”。
从湖北黄梅山村里走出来的贫家子弟谢天佑,始终有着浓重的“农民情结”,密切关注乡村经济的一动一静。这就不难理解他在1959年“反右倾”党内“交心”活动里,妄议“人民公社”在“三面红旗”中可要可不要,受到党内纪律处分。1978年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及其扩散的消息传来,天佑非常激动,说有“天亮了”的感觉;到温州模式冒出,更激发出了一种美好期望,商品经济可以救农村,农民摆脱贫困不是梦。
因此,陈先生的提示,在他不仅没有任何心理障碍,闸门打开,江流倾泻,一发而不可收拾。从1980年起,先后写作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个体农业经济和赋税剥削率》《中国封建社会的再生产与农民历史作用》《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重评西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直到我与他合作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都是对陈先生指示的研究路向的积极回应。
无论在“高潮”与“后高潮”时期,天佑有关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基本观点没有多大变化,正面肯定为主,也有一些“历史主义”的负面评点。在收尾阶段,1986年第5期《安徽史学》发表的《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的研究》,应该是他最后总结性的“定论”。
在文章中,与其他诸家相比,他注意到了“生产斗争”这条线索,主张“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生产斗争是根本动力”,两条线并行不悖,为他在80年代发表的诸多从经济角度谈农战史的论文作了注脚。
文章最后总结,又郑重地说:“过去孤立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将它强调到不恰当的高度,这无疑是错误的。但是,因此而厌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忘记它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之一,看不到这个学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它的意义并未完全消逝,这无疑也是错误的。”
在农战史研究会里,我和九生都是跑龙套的角色。掌门人富战斗精神,私下里我们谑称其为“农民领袖”。秦晖因提出“关中无地主”,触犯阶级斗争原理,遭到会长迎头训斥,声色俱厉,就是个教训。
我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过,农民战争最大的历史作用,就是死人。地主、官僚死了许多,但死的人最多的依然是农民。不管怎样,因此发生了战前不可能有的结构改观,人地关系变缓和了,王朝政府精兵简政了。君主独断,死而复生,六道轮回,徘徊不前,农民战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话,无论如何不会在“农民领袖”面前瞎摆谱的。天佑知道我的意思,在我们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里用学术的话语委婉地表达了,天佑对此没有异义。
在学术上,天佑喜欢争论,例如与杨善群在兰州激辩朱元璋做皇帝,坚持这是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杨认为朱是代表农民利益的皇帝),非常执著,但并没有以势压人,还是通过了杨的学位论文。高昭一先生误听了小道消息,说的不符事实。杨是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而不是历史系,与我们并无交集,答辩时都是第一次见面,“同门倾轧排挤”之说无从谈起。同期答辩的葛金芳、秦晖等都可以作证。
“有渐无顿”,学术史变迁路向,有历史性的承续,也有对过往的扬弃。进入80年代,天佑内心世界的活动比较复杂,隐含有多重思绪交织。他舍不得割断农战史情结,但不满意停留于重复研究、无有新开拓的僵局,希望寻找到“转型”的路径。最后,他与孙达人不谋而合,都想到了打开“中国农民问题”这一历史枢纽,以求给旧课题输入新的生命力。
1986年,他对自己思路的转变有过一次总结,说道:“直至今日,中国仍然是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农民战争诸问题往往与农民问题胶织在一起,不时召唤到现实生活中来,吸引人们去思考它,研究它。不承认,不理睬,行吗?不行。往往是欲罢不能。我始终相信农民战争史这门学科是有自己的生命力的,是会向前发展的。”(《泥径鸿爪》前言)
在50-60年代党的教育方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导下,我们这一代人,即使后来从事历史研究,也仍然具有强烈的“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养成了关心天下大事,对时事变动十分敏感的习性。
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后,天佑对国内经济趋势的诸多变化极度关注。80年代下半叶,天佑变得非常急切,一连写了《商品与道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两个阶段》、《商品的断想》、《商品发展引起的阵痛》等时论性短文。到1987年12月,在《解放日报》“新论”(内刊)上将自己的见解凝聚为“德、赛、康三先生应该同行”。
他对自己的见解充满自信,说道:“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则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则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商品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序,民主也发展到什么程度??????哪里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哪里民主空气比较浓;哪里商品经济不发达,哪里民主空气比较稀薄。放眼看辐员广大的中国,不正是这样吗?”(《解放日报》“新论”第143期)
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要到进入90年代,政经两界方慢慢发声,到邓公“南巡讲话”形成为中央统一意旨。天佑未及见到,但他的“康先生(Commodite Economy”呼喊,比形势超前了几步。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天佑的说法不够专业,也还没触到根本点子上(经济体制)。说到这里,就需要对天佑的传世代表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与以上心思的关联做点交代。
天佑是个勤于独立思考的人,执著倔强,多个场合宣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每有发言,逻辑性强,务去陈言滥调,直言无忌,不知者以为是傲岸,好出人头地。从1978到遽然离世才十年,长长短短写了大约五、六十篇文章,思绪如泉涌,一时喷突而出。除了从“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两条线结合深化开发农战史研究外,读史札记、经济时评以及为《内刊》《新论》写的国内政治问题新见,构成三大版块,现实感都很强。
其中,1986年7月26日给《解放日报》“新论?未定文稿”写的题为《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影响最大,很快被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选中,予以全文转载(9月30日第666期)。在“编者按”和继后感谢作者的信中,都肯定了该文有助于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现实意义,说“史学文章引起党政部门和干部的重视,目前还不多见,而你的大作即为一例。特此祝贺”。
对此事,天佑极度兴奋,看得很重,遂决心在陆续写成的散篇基础上,重起炉灶,提升为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系统性的史学论著。于是就有了三易“提纲”,吉林文史出版社的急迫约稿,于是就有“才未尽也呕心死”的悲剧结局??????留下的仅是半部谢氏“论语”(原提纲40节,仅完成20节)。
一方面热烈欢呼商品经济“复活”,亲赴温州现场考察,写下《神奇的纽扣》、《温州农民确实富了》等短文(1987年秋),且歌且呼;一方面却不断撰文揭露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笔笔带血,隐有忧虑。不相干的两类写作,内在应该有一种关联贯通。据我观察,越到最后,揣摩天佑内心世界,一种不祥的忧虑隐隐滋生,变得凝重:上层建筑假若没有同步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变革是“不牢靠”的。他一再指出专制主义在中国有数千年传统,根基深厚,“官场上盛行讲假话、讲违心话之风,实质上是畏惧专制独裁的心理状态的表现”。
1986年《理论内参》“理论观点”刊登了他的《学术领域不宜提反“自由主义”》,直言其忧:“若是在学术领域中,来一个反对自由主义,或开展一个反自由主义的运动,岂不是又将这令人向往、令人振奋的自由收回去了吗?哪里还谈得上学术无禁区呢!从逻辑上就是对学术研究无禁区的否定,或者说所谓无禁区是名不副实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重新考虑。”(《理论内参》第七期)
最后的十年,天佑的写作近乎疯狂,日以继夜,动笔不辄,不像过去那样从容淡定,似有“时不待我”的急迫感。说实话,当时我并不理解,或许因为热衷补习外国人的“新论”,我的注意力在彼不在此。天佑心里有一个宏愿,对家人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了,而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还没有。我要写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的时间太少了!我能把我要写的书都写完,我活得就够本了。”?????
病逝前一段时间,系里开会,他手里都拿着书,或沉思,或看书,反常地不再发言,旁若无人。犹记得“中风”前几天,系里开会,他手里拿的是王曾瑜的《岳飞新传》。我好奇问道:“怎么想到读王曾瑜的书啦?”他笑笑。现在才知道,他是在为第21章准备材料、酝酿思路,不料戛然而止。《岳飞传》和手稿残篇还摆在书桌上。
4月24日傍晚,到礼堂看电影。《红高粱》散场,大女儿回来说谢伯伯坐在她身边(教研室每人一票)。话音刚落,那头电话响起,他夫人让我赶快过去。到谢家,见他坐在书桌前藤椅上,神智仍非常清醒,低声说:“老王,我半边身子没知觉了!”我们都料不到,他自己更没有想到,神情露出丝丝不易被觉察的悲哀,我心里想:他或许已经准备好下半辈子可怜兮兮地坐在轮椅上写书,继续写完他要写的所有的书??????
追悼会上,前排左起为苏渊雷、戴家祥、陈旭麓、沈起炜等先生
1988,我连续遭受天佑和陈先生遽然去世的巨大打击,参加了两次撕心裂肺的追悼会,其间只隔了半年多时间,心理和生理濒临崩溃边缘,形容憔悴,亲近的朋友怕我支撑不住。50岁的我,第一次尝试参透生死。到2011年,老伴弃我而去,精神上坚强得多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岁上,真正彻悟到了必须接受“总有一死”的无上真理,谁都不可能例外。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80年代初,我与天佑一样,热切期盼“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终结千年“颠沛往复”的苦境,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开新局,洋溢着对未来的乐观期待。然而,相对无边无际的历史长途,人生太过短促。穿透历史奥秘,寻找“长生不死药”以医治人类所有病症,最多只是个美好的奢愿;旧病有了良药,《本草纲目》不见的各种怪病又出来继续折磨人。四年之后,拿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重读,现实的场景在心头浊浪翻滚,心境忽然变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前此跳过的灰色语句格外剌眼:
“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的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此文以《哀悼韦伯的精神分裂》为题,发表于1992年第1期《探索与争鸣》。
至于今日,我们又明白了许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仍需要重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尚在书写中,历史不会停步,学问殆无止境??????什么是健康的市场经济?什么是变态的、畸形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历史不断展开中才会慢慢露出它们的真容,为我们展开新的认知世界,不断提高鉴别和预判方向的智商。天佑的学术追求已经留于汗青,“讲真话,不讲假话”的求是精神长存,同时也再次证明学问家唯有透过社会前进的曲折历程,才能不断改善自己的认知,拷问世界也拷问自己。书是永远写不完的。如果天佑在世,我想,他也会这样看的。
写于2018年清明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