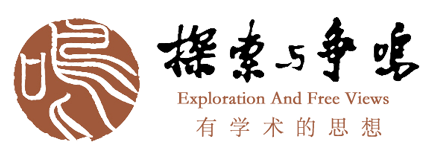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我为还布哈林以历史清白所做的工作
叶书宗
作者 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苏联史领域,就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的一统天下。这本书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写成是个长期隐藏在苏共党内领导层中,干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国家勾当的帝国主义间谍,终于在1938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得到应有的惩罚。“文革”期间,全国更是大批、特批“中国赫鲁晓夫式人物”是“比布哈林还布哈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同时,城乡则到处反反复复地放映苏联的革命历史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对观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两部影片中有个突出的人物:形象委琐、阴险恶毒,是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暗杀列宁,致其差点儿丧命的同谋者。影片中的这个角色,就是布哈林。苏联这两部影片,确实称得上是以电影艺术的形式,具体地、形象地塑造了布哈林的内奸面目。因此,在中国,只要看过《列宁在十月》,或者《列宁在1918》,即使没有读过《教程》,对苏联历史不甚了了的人,都知道布哈林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1955年,我在大学读书时,政治理论课《马列主义基础》的教材就是《教程》。那时就觉得像布哈林这样的人,怎么能长期身居苏联党和国家的高位,真是不可思议。1961年,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班读书,更觉得布哈林虽然于1938年3月5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死刑,15日被执行枪决,但是对《教程》那样写布哈林,更是心存疑虑。
1976年初,我看到一本辑录的、供大批判用的《布哈林言论》(通称“灰皮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布哈林的著作。虽然编者也是有目的地摘录布哈林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言论”,可是反复读这本书,我越是想从中找出布哈林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观点,越觉得布哈林说的符合当时苏联历史的实际,并且政策性地解释了列宁来不及解释的新经济政策。
经历了“文革”的洗礼,我以“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作为自己史学研究的追求和人生价值的体现。因为我觉得,真实的历史是民族复兴的文化传承,是社会进步的文化底蕴,是思想之花绽放的必要土壤,更是国家强盛的精神支柱。
在多年的史学研究中,我总算逐渐领悟到:历史虽然是记录过去,却能感悟未来;历史虽然已经画上了句号,却蕴藏着无限。我决心解开“布哈林之谜”,作为自己史学研究的新起步。不过,“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实在是一条崎岖的求索之路,内中的酸、甜、苦、辣,可能只有我自知。
要想解开“布哈林之谜”,当时能找到的资料,实在是十分困难,而且少之又少。我选择重新细读《列宁全集》,从中梳理列宁与布哈林之间的意见分歧、争论,以及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等等。我将所有这些内容,都抄录成卡片,并以此为基本线索,逐步拓展。这样,终于大致搞清布哈林究竟是怎样的人。
布哈林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开始阅读、研究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尤有深入研究,1906年加入苏共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哈林小列宁18岁,与列宁是忘年交,也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列宁虽然同布哈林有过多次争论,但是非常喜欢这位年轻人。
每当列宁谈到布哈林时,总是不吝褒奖。特别是1922年12月24日,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续一》中,对当时俄共(布)中央的六位领导人,作了综合性的、总体性的评价。列宁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等六人,是这样评价的: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
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就是较有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行政方面。”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皮达可夫“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他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不能指靠他的。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的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4卷,第745-746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
列宁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在1922年12月中旬,第二次中风,半身瘫痪,丧失独立工作能力的情况下,给全党留下的最后的话。
“鸟之将死,其声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列宁自忖已将不久于人世,他最担心的是党的事业。列宁不顾医生不许他工作的禁令,终于争取到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给代表大会的信》,即通常所说的《列宁遗嘱》,就是这样留下的。列宁根据他一生的观察,之所以对上述六人做这样的评语,完全是从党的事业出发。
因为列宁知道,如果不说,再也没有机会了。列宁谈到上述六人,言语之间,既严肃,又充满慈爱和关切。特别是对布哈林,列宁多次、反复赞扬他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我觉得,列宁对上述六人的综合评语,如果换成5级分制打分的话,那么就是:布哈林4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3分;斯大林2分。
事实也确如列宁所预见的那样。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出色地阐发了列宁来不及展开阐述的新经济政策,规划了苏联(原来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另一种模式。布哈林的理论和著作,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财富之一。可是,布哈林被冤杀之后,他的著作也被列为必须焚毁的“禁书”之一。
“文革”后期,我接触到布哈林的著作,尽管只是零星的“碎片”,也禁不住惊叹:怪不得列宁称布哈林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而《教程》却这样肆意往布哈林头上泼脏水,这样刻毒地咒骂布哈林,并铁定布哈林被当做“帝国主义间谍”处死,是应得的惩罚和结局;这不是在骂列宁嘛!
我既然走上“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这条路,就一定要还布哈林以历史清白。我选择的切入口是“三仙巷事件”。上文已提到,苏联那两部历史电影,在中国的影响极大,又很坏。我觉得,作为苏联历史的专业研究者,应当,不,确切些说是有责任在我国人民大众中澄清历史事实,消除这种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不好影响。
应当让我国人民大众明白:像布哈林这样潜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8岁就参加苏共,投身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领导过1917年莫斯科武装起义,参加创建苏维埃新国家的人,怎么可能当苏维埃国家刚刚创建起来,又去参加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呢?布哈林又怎么可能参与谋杀列宁呢?要让我国人民大众明白:《教程》是凭政治需要任意编造历史,进而从根本上动摇《教程》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信任度。
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由于朋友的帮助,我终于找到可信的有关史料。这些史料足以表明:布哈林不仅不是如《教程》所写的,以及《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这两部电影所表现的;恰恰相反,布哈林参加了平定1918年7月6日,社会革命党策动的“三仙巷事件”的战斗,他本人也成为社会革命党人暗杀的目标之一,被暗杀者从暗处扔过来的炸弹炸伤。
《教程》和苏联电影所表现的关于布哈林参与谋杀列宁事件,事实也并非如此。历史的事实是:1918年8月30日,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遭暗杀。消息传到莫斯科,当天中午,布哈林正好在列宁家里吃中饭。当布哈林得知列宁已安排好当天晚上将去巴斯曼区和莫斯科河南岸区演讲时,就竭力劝阻列宁取消这一安排。但是列宁不想改变这一安排。为了使布哈林放心,列宁就有意把话题扯开,并说他也许不去了。
当晚,列宁还是按原计划到米哈里逊工厂演说,结果遭到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的暗杀。在列宁遭暗算的事件中,事实表明布哈林是非常爱戴列宁,关心列宁的安全的。
1979年底,我根据已收集到的、确凿的历史事实,撰成《布哈林不是“三仙巷事件”的策划者》的文章。我在文章的末段写道:“本文当然不是评价布哈林一生的功过,只是指出,在‘三仙巷事件’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作者,不顾历史事实,而是根据权力意志和打倒布哈林的政治需要,硬把布哈林写成‘三仙巷事件’的制造者。哪怕布哈林的一生犯有一千桩罪行,这种写历史的方法也不是科学的方法!
一个人犯了错误(或者犯了罪),就把他的名字从历史活动的舞台上挖掉,把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加到他的头上;反之,一个人如果有了成就,从此把他的错误列为全社会的忌讳,把一切好事都加到他的身上——史学研究中的这类做法是以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写历史的腐朽的史学观点的反映。”
我知道这篇文章可能遭遇的风险,因此自己反复阅读,认为引用的史料确凿、可信;提出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80年元旦后,我把文稿投给国内某家颇有影响的史学杂志社。我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甘冒风险,写成这篇文章,就是想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史学研究应有的严肃和尊严。可是,大概过了四天,文稿就被退回来了,而且没有一个字的说明。
对于文稿的被封杀,我有心理准备;而这么快就被退回,却有点儿吃惊。不过我并不灰心,而是继续细心地阅读能够找到的布哈林的著作,研究布哈林的真实思想,以及他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争论,又怎么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处死,精心撰写这些方面的文章。我深信:事实终究是事实;谎言终究还是谎言。
1980年4月初,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的“当前世界史研究动态”学术研讨会。当时,朱庭光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不久即任所长),主持这次会议。庭光同志14岁就参加新四军,是中苏论战和国际共运大论战写作班子成员之一,有极强的党性和高深的理论修养,是当时世界史领域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
我向会议提交了一篇《当前国内外关于苏联史研究状况》的文章,并在会上重点谈了关于布哈林问题的研究状况,还说写了一篇关于布哈林问题的文章,寄给一家杂志社,几天就被退回了。庭光同志就说:“把文章寄给我们看看嘛!”会议结束返沪后,我就把《布哈林不是“三仙巷事件”的策划者》一文,寄给世界历史研究所。很快,文稿在《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上刊发了。
这篇文稿刊发后,在世界史领域,甚至在社会上都产生一定的震动。多家报刊摘要刊登这篇文章的内容。对于这篇文章,庭光同志后来这样评论:“在世界史研究的刊物上第一个起来为布哈林局部翻案的是本书(指《布哈林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另一作者叶书宗,他与人合作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三仙巷事件’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作者,不顾历史事实,而是根据权力意志和打倒布哈林的政治需要,硬把布哈林写成是三仙巷事件的制造者。”(朱庭光:《布哈林研究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布哈林传序言〉》,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
由于这篇文章在史学界,乃至在社会上的动静比较大,有“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势,国内同仁甚至戏称我为“叶哈林”。
接着,1980年10月22日,《〈解放日报〉新论》第1期,刊发了我撰写的《恢复布哈林的本来面目》一文。《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2期,发表了我撰写的《让历史来公正地裁决——布哈林功过问题我见》。上述两篇文章,是我在较为深入地研究布哈林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评价布哈林的一生。对于《让历史来公正地裁决——布哈林功过问题我见》一文,庭光同志完全肯定我在这篇文章中对布哈林的认识和评价。庭光同志写道:“隔了两个月,他(指叶书宗)又发表了对布哈林试图予以全面的重新评价的文章”。
接着,庭光同志就转述我在该文中对布哈林的总评价:布哈林“是一个犯过许多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的主要错误是发生在十月革命前后,而从1924年列宁逝世后,直到1929年他被当作‘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富农代言人’加以批判斗争的时期,恰恰是他多年从事理论研究、从事苏联社会的实际调查,提出许多独具慧眼的卓越见解,并敢于向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不同意见的大大值得肯定的时期,是他一生中对革命最有贡献的时期。”(见《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
那几年,我还应邀到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校,为历史系大学生讲布哈林的悲剧一生,以及我为什么要研究布哈林。我希望大学生们能从中体会:认识布哈林的悲剧一生,是认识苏联历史,特别是认识斯大林当政时期的苏联历史的一把钥匙。我的讲课都引起积极的反响。我觉得,如果连大学历史系的讲台都不敢讲真实的历史,听任谎言荼毒青年大学生的思想,那不仅是历史的悲哀,更是教历史课的教师的悲哀。
1984年,我为《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写了一本通俗读物:《杰出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布哈林》。这本通俗读物被收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合订本——一),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间还曾为朱庭光主编、沈永兴副主编的《世界历史名人谱》(现代卷),写了一篇介绍布哈林一生的文章。
1988年,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闻一研究员合著的、300千字的《布哈林传》,在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闻一研究员是我的挚友,既豪爽、又热情;特别是他精通俄语,连俄国人都称羡。起初,我和闻一商量:我们分工合作,写一本180千字左右的、通俗的布哈林传记,在我国人民大众中形成布哈林的真实的历史形象。因此,公开出版的、既丰满又深刻的这本《布哈林传》,主要应当归功于闻一研究员。
30万字的《布哈林传》出版后,我曾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写〈布哈林传〉?》的文章,表达我们写作这本书的心灵冲动。我在文章中写道:“我敢肯定,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希望扮演悲剧的角色。然而在艺术舞台上以及文艺作品中,人们却喜欢悲剧,因为悲剧是如此强烈地震撼观众和读者的心,给人以震惊,并启发人去思考。人们之所以偏好悲剧,除了享受悲剧特有的艺术感染力和进行反思以外,恐怕谁都明白,艺术舞台和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悲剧,是现实生活中随处都有的悲剧的典型概括。”(叶书宗:《我们为什么写〈布哈林传〉?》,载《苏联历史问题》1988年第4期)还布哈林以历史的真实,写布哈林悲剧的一生,是为了后人能理性地认识那个时代,理性地认识斯大林当政时期的苏联历史。
1988年是布哈林诞生一百周年、被冤杀50周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定:撤销当年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布哈林等人的判决,宣布为他们平反。2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恢复布哈林的名誉。5月1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恢复布哈林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称号。6月21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布哈林的党籍,肯定他“积极参加十月革命,革命后曾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贡献”。历史最终是严肃的、公正的。这真是:湛湛青天不可欺!
上世纪80年代末,闻一研究员访问苏联,带去我们合著的《布哈林传》。闻一在苏联访问时,特地拜访了仍然健在的布哈林的遗孀拉琳娜。拉琳娜非常高兴和惊讶,看到中国的史学家能够不避嫌疑,主持历史的正义,写出研究布哈林的史学专著。她赠送给闻一和我各一张有她亲笔签名的照片,由闻一带给我。
经过十年的艰辛,我在苏联史的研究中,终于做成了这件事:还布哈林以历史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