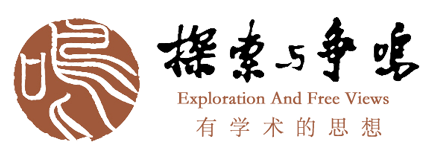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古典的黄昏——对当代青年古典学者普遍焦虑的反思
编者按 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后,大量的年轻学人作为新鲜血液被补充到大学教师队伍,他们被戏称为“青椒”。“青椒”群体学历光鲜,产出惊人,对所在高校的学术成绩贡献十分可观。他们是莘莘学子的职业梦想,是学术世界的明日之星。然而,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他们为何选择学术道路?有何学术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生存现状如何?如何看待和实践自己的学术发展之路?
关注中国未来学术发展,关注“青椒”群体,《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推出“青教心声”专栏。本专栏推出后取得了一定关注,一些高校青年教师纷纷来稿,他们分别从自身视角,于字里行间展现当代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状态。本专栏将陆续刊发专稿,透过诸多个体的亲身经历,多方位展示“青椒”或辛酸或坚韧的心路历程,诉说这一群体的心声,力求为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的进步,提供第一手资料。
2013年,青年古典文学学者张晖因急性白血病而不幸逝世,引起人文学界的轩然大波。不少业已功成名就的学者纷纷表示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大损失。其中也有人认为,“张晖之死”构成了一种对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生存环境的无声挑战。三年以后,与张晖师出同门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青年学者李思涯因“晋升被蓄意拖延”在公开场合殴打博雅学院院长甘阳,最终被关进拘留所,引来网络热烈讨论。
有人批评李思涯打人之举“斯文扫地”,也有人觉得李是在对当下不合理的学术晋升体制进行反抗。张晖与李思涯共同的导师蒋寅曾以“金陵生”的笔名为李思涯辩护,认为李思涯具有相当充分的发表成果,进而具有优秀的学术能力,与张晖不相上下;李思涯得不到晋升,显然是遭到了不公的待遇,其打人的暴力行动自然也就有了“正义”的属性。
同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张晖因疾病与贫困而在逝世后成为大众热议的话头,李思涯则因过激的暴力行动被众多吃瓜群众推上“反抗”的战斗舞台。如果将这两个鲜活的案例摆放在一起,不难看到,中国古典学者身上一度具有的安贫乐道、箪食瓢饮的高尚形象正在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现实主义生存悲剧,及其背后的体制性难题。对于许多投身于古典学术研究的青年人来说,由于无法在这个日益世俗化的时代找到有效方法安顿自己的身体与灵魂,他们难免陷入一系列的恐慌,担心自己要么像张晖那样英年早逝,要么像李思涯那样成为“革命小将”。就此看来,以传承斯文为信仰的“古典青年”几乎被抛入到了一个残忍的现代学术“江湖”当中,成为了漂泊拼杀的“古惑仔”,要么“一脚踏进救护车”,在身心方面遭遇着种种病理式的困扰;要么“一脚踏进拘留所”,在当代学术体制铁板一块的生存处境中等待着“重见天日”。
正如近日以来关于人文学者生存艰难的众多议论所揭示的那样,科研评价、职务晋升等机制的弊端是导致青年学者生活不幸的直接原因。与实用类的工科和社会科学不同,人文学科的非功利化特征决定着其中的高端研究必须依靠国家或社会资本的不计成本收益的投入,这也就决定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文学术研究同样无法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抗衡。东部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南京等地在作为人文研究重镇的同时,其较高的消费水平和巨大的竞争压力也给青年人文研究者增加了巨大的压力。
据一位在南方某一线城市知名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刚刚取得教职的青年教师反映,其年工资净收入不超过十万,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补助,唯有通过申请课题、发表文章来填补家用,由于家庭条件本属清贫,要在良好地段买房根本痴人说梦。为了能够早日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这位朋友不得不长期在外面的“读经班”和“考研辅导班”中从事兼职,以至于长期处于备课、上课的节奏,无法抽出足够的时间沉浸在经史子集中,提炼出精彩的研究成果。
这一现实困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文研究者当中抑郁症、躁郁症等各式各样的心理疾病频发。一位北京顶尖学府的博士生曾经对笔者透露,他们院系里许多博士甚至是硕士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轻度的表现是失眠、饮食失调等,病情严重的则大多要依靠重剂量抗抑郁药物维持基本的作息正常,以至于影响到身体的其他机能,甚至造成极端严重的物理性疾病。在该校的博士生宿舍的垃圾桶中,时常可以看到抗抑郁药的药瓶。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反映,引发抑郁症的原因有许多,科研发表、求职与毕业论文写作的压力在其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过去常常说人文学术是“养人”,是滋长“浩然之气”。现在的学术则因其僵化的评价模式不断破坏着学者、学生们的身心健康。
除此之外,学风的大变革也让学术界日益变得浮躁、浅薄且僵化。在中国古典研究界,以发表效率为目标的研究风气带来令人担忧的局面:一些学者把“动手动脚找东西”发挥到极致,以至于不去区分东西的好坏和重要程度,过度夸大一些无名之辈或是海外印刷物的历史与思想价值,以便让自己尽快就手头独享的生僻材料写出论文;另外一些就引用各式各样的时髦“理论”——尤其是西方某些汉学家“夹生饭”般的中国解释视角——来“重新发现中国”,甚至挑战中国人的一般常识。
从学术整体而言,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偏僻的人物与史料,也需要知道海外汉学家如何评价中国。但是,这两种路径没有任何理由成为古典研究的主流,甚至挤压到经典作品、人物和专业基础问题的研究空间。不难想象,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将来必然不会再把面向广大学生的文化基础教育视为工作重心,更不会回到经典本身品尝其中的精髓并发现真问题、真线索,而宁可把自己变成“论文技工”或“文献掮客”,在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洋洋自得地走向不可救药的庸俗。
与这种学风变异相关的现象就是教育本身遭到冷落。在过去的大学讲堂上,真正优秀的学者是以培养学生、传承文明核心精神为己任的。民国大家章太炎门人满天下,黄侃、钱玄同、周氏兄弟等名字家喻户晓;熊十力弟子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也各有所称;南大千帆老人的“程门弟子”,更是体现出当代中国古典学术界为数不多的活力。相比之下,如今的许多老师宁可花时间去发论文、做项目,而不愿意用更多的时间亲近学生,不传授真正的古典知识和学术方法,也不愿意了解学生的精神状态,并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加以引导。
长辈学者们放弃这种手把手教育态度的根源,在于人文学科自身的结构化转改:未来的中国不需要那么多人文研究者,不需要那么广阔的“传承”与“队伍”。因此,有必要让其中大多数仅有热情、但无才力的人知难而退,教学中的“放养”和刻意施加的压力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通过这种冷酷考验的筛选后留下的,将是看似最为优秀的那些人。这等于说未来的人文学术必然会逐渐缩小规模,最终变成少数地区的少数人的精英化活动。
既然如此,在本科、研究生的课堂上十分细心地传授知识也就成了徒费心机。老师们十分清楚,堂下坐着的大部分学生(哪怕是硕士、博士),未来与古典学术一点关系都没有,相比之下,他们更应该去学习一些当代实用的知识;甚至最终从事学术者,也以会一些通过论文灌水来实现实用目的的手段为荣……显然,这种风气对少数真有学术潜能的人十分不公平。至少,这种刻意施加的选拔压力最终将造成一种压抑且残忍的氛围,让本应静心养气的人文学者陷入心魔不能自拔,或是陷入抑郁,或是采取过激方式争夺一己利益。这样一来,中国古典思想的基本旨归——良好的涵养——也变成遥不可及的幻想,整个古典研究进而面临着“黄昏”的窘境。若是未来的“接班人”失去了内在的精神活力,那么不见五指的“黑夜”也将迅速来临。
为了在缩减规模、提倡精英人文教育的今天保持竞争力,人文学科的博士、青教必须拼命“做任务”,给自己增加“基本分”。问题在于,许多愿意将青春交付给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的年轻人一开始的诉求并不是成为这种机械生产的作业员,而是实现一种审美化、趣味化的生活,在精妙的义理与辞章中获得生命的升华。基于这种动机而投身古典研究的青年们最终发现,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都与自己热爱古典、热爱中华文化的初心相违背,最终,一次次学术考核、答辩和求职应聘的失败无情地戳破了他们这种近乎于乌托邦式的幻梦,把他们摁在经济与社会金字塔结构的冰冷边缘。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问题并不出在现实太过残酷,而恰恰是在于他们一开始太过理想。实际上,在学术研究的开端,严肃的教育者就应当用当前的残酷局势提醒学生要保持清醒与批判意识,能够用理性的甚至是冷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未来,不要贸然投身到与自己的性情和初衷并不吻合的“研究生涯”当中。
青年古典研究者遭遇的尴尬处境,也是对这个时代整体上文教凋敝、结构紊乱格局的一个微观反映。反过来说,初心不可失去,但更需要强劲有力的身体与开朗豁达的心态去坚守。对于每一个真心从事古典研究的青年人,他应当首先冷静反思: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一行当?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勇气与魄力去面对接踵而来的庸碌且无情的挑战?自己到底能不能“顺势而行”、“任意东西”?如果无法以“邦无道则隐”的达观态度侧身红尘,再多的“好古”热情最后都会凋零。相反,如果能够真正在古典中找到对“此事古难全”的透彻领悟,进而发展出尼采所谓“批判的古典学”的研究心态,相信青年们会找到一条别样的桃园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