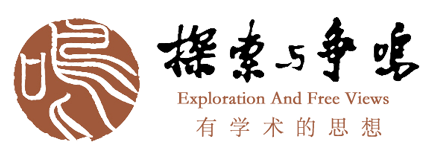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反对听觉新霸权
——兼与周志强和王敦教授商榷
刘昕亭
内容摘要 在听觉文化研究已经于西方学术界遍地开花之际,一个中国本土的“听觉转向”正在兴起。听觉还是声音?听觉文化研究还是声音政治批评?结合当下有声出版、智能语音助手和听觉营销等“听觉中心主义”的新态势,正在勃兴的声音研究不是亦步亦趋地仿照既有视觉文化研究,递进地将听觉提升至新霸权地位的范式类比。齐泽克等理论家开拓的声音的激进化道路,正在努力超越“语言学转向”以来的范式,寻找破解主体形而上学的新理论疆场。
关键词 声音研究 听觉文化 齐泽克 周志强 王敦
作者 刘昕亭,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广州51027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当代文论与‘去黑格尔化’研究”(13BZW004);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文论创新与经典重译”(GD12CZW10)阶段性成果
某种“听觉转向”在“视觉转向(visual turn)”持续数十年的理论热潮后,正在引领新的学术时尚,理论范式、概念争议随之而起。周志强从持续关注“中国好声音”等音乐娱乐节目,延伸到对当下流行文化声音景观的文化政治批评;与之针锋相对的,是王敦以“对声音和听觉这两个关键词语的辨析、取舍”,“听觉文化研究”和“声音政治批评”的所谓“互补”,坚持“话语建构的关键课题”①。这些论争中浮现的问题,既是对全新视听环境的学术回应,又召唤着新的理论资源与学术范式。
笔者认为,王敦通过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类比,建立听觉文化学科范式的构想,正同步于听觉市场的新运作,可能落入以听觉霸权取代视觉中心的陷阱。而周志强要求以声音的政治批评,刺破日益膨胀的“声临其境”的主体泡沫的批判立场,不仅忽略了声音自身的多意性和幽灵性,亦低估了声音转向背后对新学术范式的探索渴求。就在周志强和王敦两位学者基于各自既有的学术兴趣展开商榷之际,有关“声音研究”和“听觉文化”的论辩同时在西方学术界回响。参考国内外理论界近年来对声音/听觉的论辩,尤其重视这一转向的市场和技术驱力,笔者认为听觉文化/声音研究的崛起,既是对视听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回应,亦是借由“本体论转向”“以目听之”等新理论探索超越“语言学转向”,在21世纪的听觉市场中寻找破解主体形而上学的新路径。
听觉市场的兴起:市场、技术
与文化产品的变局在相关研究已经于西方学术界遍地开花之际,一个中国本土的“听觉转向”正在兴起,且其“中国路径”明确显现为叙事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爆炸和话语激增。[1]然而,就在学术研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拥抱声音这支绩优股的时候,资本市场也在野心勃勃地以耳朵引领新的“出埃及记”。资本投入的新动向、技术进步的新挑战和视听产品的新开发,都在遥遥呼应甚至挑战学术话语与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我总结为市场、技术和文化的三个新趋势。
首先是新的听觉市场的形成。眼下“音频营销”已经成为全球市场营销学的新贵,各大奢侈品产业都在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音频品牌,生产能代表一个品牌身份和价值的独特声音,以期消费者在听到一个特定声音的时候,就准确识别、想起乃至购买某一品牌[2]。其次,这一市场拓展的新动力直接来自有声读物(audiobook)、播客(podcast)等音频付费电子产品急速扩增的盈利、人工智能支持下的虚拟语音助手的迅速推广,以及声纹识别(VPR)作为生物识别技术黑马的无限商业潜力。最后,在市场营销、技术升级之下,视听文化产品正在建构新的声音/听觉的政治。在大陆青年亚文化中,声优、直播、抖音和喊麦等新视听文化的流行,都不再局限于阿多诺意义上单纯作为粘合剂的流行音乐的社会功能。
置身这一市场、技术和美学的转变中,当学术界热切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开拓新的批评战场之际,回顾和评估持续数十年的“视觉转向”似乎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根据视觉艺术史专家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的研究成果,就在“视觉转向”引领的重新发现观看的数十年中,人类的观看能力却呈现吊诡的瓦解趋势,“人的心理状态和感知能力都在下降”。[3]换句话说,发现视觉、转向视觉的过程,同时是主体能够看到的事物越来越少,或被主体看见的“可见性”日渐匮乏的过程。莫雷·谢弗(R. Murray Schaeffer)的研究同样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的听力退化,“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欧洲人听到和注意到的自然声响(nature sounds)从43%下降到20%……虽然经过技术处理的声音的激增并未引起注意,但是沉默的减少已经被广泛承认”[4]。如果19世纪“新的流通、传播、生产与理性化模式,均要求并塑造出了一种新型的观察-消费者”[5],那么今天资本借势新的技术突破,正在重新规划和殖民主体感官,建构新的耳朵的“知觉的悬置”,这就是周志强从摇滚乐之物化噪音、流行音乐之人机共声与梵音音乐之去声音化等声音景观中体认到的“听觉中心主义”的新变化。
于是,今天理论工作者们的挑战在于,如何获得新的批判位置与批判话语,如何在被听觉营销包围的资本重音中辨识另类的音调。声音/听觉所激发的无限学术想象力是学术共同体对一个新的听觉市场和声音政治的紧迫回应。当我们掏出手机命令Siri将明早的闹钟调整到6点,听着Alexa通过人工智能合成的“深度音乐(deep music)”,距离拉康和德里达们在打字机前敲下他们的经典代表作,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技术资本主义和全球科技巨兽正在以理论家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将人类拖入视听的新情境中。无论中西学术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正是“摆脱术语的争论,并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声音的审美和政治潜力”。[6]
声临其境:从语音中心主义
到听觉中心主义周志强和王敦基于各自研究,发出了这一新兴领域的“中国声音”。简单来说,周志强要求以一种声音的政治批评来反思日渐显露狰狞面目的“听觉中心主义”,王敦坚持传统人文主义的听觉文化,即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聆听者在具体的接收语境中进行多样的商榷和解码;周志强将这一对立指向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文化研究的范式之争。那么耳朵,究竟是一个有待批评利刃解剖的怪兽,还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求真对象?回顾西方文论对于声音/语音的理论探索,或许有助于剖析眼下“听觉市场”正在孕育的这一新“听觉中心主义”。
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曾以对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的批判发动对整个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猛击。在德里达看来,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认为声音和语言较之书写文字更为优越,也更为重要;因为当人们在言说时,思想与言说直接同步,语音显示着主体的直接在场,使意义获得了同一性保障。德里达提供的解构主义策略是利用书写文字的模糊性、歧义性乃至差异去颠覆语音的精确性与同一性。德里达这一基于西方二元对立哲学传统的解构理论,显然不具备放之四海皆准的效力,如中国“书同文”的文言文传统就并非是“语音中心主义”的。有趣的是,德里达批判的语音中心主义,这一以声音的直接性肯定主体存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辑,却是今天视听文化产品发现声音、建构声音魅力的核心密码。
以眼下大热的娱乐节目“声临其境”为例。这是湖南卫视推出的一档竞技类综艺节目,演员的配音和念白成为主要竞演内容。竞演嘉宾始终隐藏在幕后,只能利用自己的声音进行表演/回应,通过展现个人独特的语音魅力,由现场观众指认/识别嘉宾本人。节目名称“声临其境”确乎实至名归。“按照此一思路,我所说的声音,尤其是这里所选取的声音,都是可以脱离肉身而得以‘自我保存’的声音,即通过违背其现场性而获得现场性幻觉的声音。这种可以自我保存的声音,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作用就是不断地创造倾听者的自我感,从而最终把外界隔绝出去。”就此周志强指出“一种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正在暗度陈仓,变成消费主义时代的听觉中心主义,而这种听觉中心主义并不是因为听觉的生理改变而实现,反而是由声音的制作技术完成的一次声音对人的成功‘欺骗’与文化‘霸占’”。[7]
无论是“中国好声音”等视听娱乐制造的“唯美主义”的耳朵,还是全球奢侈品牌重金砸入各类语音实验室,期待音频营销像塞壬的歌声一样勾引消费者的钱袋子,上文论述的听觉市场的兴起,其重要编码都在于一种古老幻觉的复兴,即选择性强化声音的沉浸式、内在性等特征,以从外部世界区隔出自己内在声音的方式,确立主体的存在。一方面是浸入、沐浴和包围的沉浸式倾听,催生出独属于我的个体内在性幻觉;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身体之外的声波震动节奏,操控某种声波或频率的政治,不断敲击和楔牢意识形态网格中的主体。身处这一声音环境中,一种自我内心/外部世界、直接体验/外来置入的二元对立,正在塑造主体的新认知体验。正如威尔·斯克里斯克的批评,“声音艺术话语受限于内在性(interiority)、浸入性(immersion)、直接性(immediacy)和连续性(continuity)”等概念,“体现出对自我存在的直接性不加批判地肯定”[8]。这一重置知觉坐标的实践,即“有意识地聆听、观看,或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物的方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性”[9],对主体知觉习惯的塑造和培养,正是过去数百年资本主义强有力地重塑人类主体性的产物。半个世纪前德里达开创了书写与差异的反击语音中心主义的道路,那么当资本、技术和意识形态对声音的处理更复杂更灵活的时候,理论如何驱散声音幻景的迷雾?
事实上,与德里达相对的,西方理论传统一直存在另一个将声音激进化的趋势,这一理论思潮迥然不同于王敦对于听觉主体重新解码的乐观,亦与周志强式的针对一个超验的“声音拜物教”的警觉拉开距离。齐泽克指出,“莫名其妙的声音的魅力,只要对音乐史投去惊鸿一瞥就足够了。音乐史通常被解读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寻常故事——语音统治文字——的反历史”,在此“语音是能指中抵抗意义之物,它代表着无法通过意义来复原的迟钝惰性”[10]。与书写之维锚定意义的稳定性截然不同,语音的随意性、多义性为能指的不确定性打开潜能:语音/声音被视为威胁了既定秩序,因此不得不被严加管制和固定成文字,听命于书面文字的理性阐释。女性主义者们更试图以声音作为检视男权文化的颠覆性视角,她们将声音作为书写的对立面,与流动的、连续的、线性的书写形式不同,克里斯蒂娃的前语言的声音自由,伊利格瑞以语音戳穿父权制文化对看的过分投入,都力争通过对声音的另类理论化道路,开辟新的批判疆场。
基于此,齐泽克指出“语音的盈余是有待决断的”[11],这意味着声音既不是等待多重解码的多义性与多元性空间(如王敦),也不是简单诱捕主体的先验陷阱(如周志强),一种听觉中心主义的新运作,可能未必如周志强所忧心的那样战无不胜,但也绝非像王敦认定的可以简单求真,它“是活死人(living dead),是从自身死亡里幸存下来的某种幽灵显灵,它是意义的日食(eclipse of meaning)”[12]。正是因为这一不确定性和未决定,丈量声音的进步指数,破解声音的魅影迷思,才成为理论工作的意义所在。
因此,我完全赞同周志强对一种听觉文化研究陷阱的警惕,但又不赞同他将这一场声音研究论争,再度还原为某种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的范式之争。两位学者你来我往的观点交锋,固然在学术范式上模糊对应着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文化研究对于流行文化的不同态度,即周志强的理论关注在于揭示一种声音景观中的权力宰制及其对主体的影响,而王敦对听觉主体的接收过程和能动解码,报以更为乐观的期待。笔者无意追溯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只想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阴郁悲观,与其学派的形成发展,历经纳粹迫害、流亡美国又恰逢好莱坞勃兴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而英国文化研究,则由一群工人阶级出身的“奖学金男孩”们付诸实践,战后英国高涨的新左派运动和核裁军运动,使得这一批理论家对于人民(the people)而非乌合之众(the mass)的反抗经历、抗争经验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抛开这一20世纪独特的革命历史进程,盲目以某种解码的乐观、消费社会的抵抗等民粹主义范式继续21世纪的解放故事,是不恰当的。在资本已经虎视眈眈殖民耳朵的时候,王敦所要求的听觉文化的“求真”过于天真,甚至可能不自觉地沦为资本扩张的共谋者,毕竟那些西装革履的市场营销经理们,比理论家们更懂得如何发挥听觉的无限潜力,只是这一潜力必须服务于资本市场的利润。在这一意义上,新世纪以来声音研究的凸显,一方面是对一个新听觉市场的思想回应,更重要的是声音研究正是要在上述结构/能动、法兰克福/文化研究的范式僵局中寻找新的突破,而周志强的回应,亦低估了这场由他自己发动的声音进击的理论意义。此间,几乎同时发生的来自大洋彼岸的学术争议,或许可以提供重写声音的“他山之石”。
反对听觉新霸权:三个拒绝与声音研究的新动态
2015年,就在周志强和王敦展开商榷之际,有关声音研究还是听觉文化的论辩同时在西方学术界回响。无论是米歇尔·霍姆斯(Michele Hilmes)“有没有一个被称为声音文化研究的领域,那重要吗?”的发问,还是布莱恩·凯恩(Brian Kane)对一种“没有听觉文化的声音研究”的探寻,争议声音研究与听觉文化的不同旨趣,尽管“只是学者们的感觉不同”,明确听觉转向的意义所在,在东西方学术界几乎同时引发争议不是偶然的,这是资本重新编码声音、安置耳朵的历史进程中,学者们遭遇的共同挑战和切身感受。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由于今日中国在数字通信、智能语音等领域处于当之无愧的“第一世界”,中国学者们的问题意识更为迫切。结合这些学界论争,尤其是西方文论从德里达到齐泽克开启的有关语音/声音的思考,我认为声音研究的重要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拒绝。
首先,拒绝按照既有视觉文化研究的逻辑,在某种类比和对应的关系中,搭建乃至复制一套听觉文化研究的新框架,这正是许多学者选择声音研究(sound studies)而非参照既往视觉研究的概念拓展出一套听觉文化(auditory culture)的原因[13]。
与王敦设想的比照视觉文化研究来命名听觉文化研究的思路完全相反,这些学者格外警惕把一套视觉文化研究的关键概念、路径方法,复制到一个所谓听觉文化研究框架中,只不过主角从眼睛换成耳朵。他们担忧在破解视觉霸权后,转而膜拜耳朵(听觉),甚至鼻子(嗅觉)亦或手指(触觉)。
在我看来,对于声音的关注,固然是王敦所倡导的完善人类感官研究意义上的理论扩殖,但这一研究不是复制既往视觉研究的逻辑,不是将曾经的边缘感官如听觉、触觉推升为新的学术高价股票。扶植听觉取代视觉成为一个新霸权感官,这不仅是学术市场的新泡沫,更忽略了(或有意忽略)耳朵正在参与的文化政治与听觉中心主义的新运作。“试图通过界定听觉文化或声音的敏感性,以反对视觉文化的主导地位”[14]是危险的,对于声音的关注,“不是试图提升感官上的弱者(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以建立一种神秘或‘丢失的’感官均衡或常识(就像麦克卢汉的目标一样),而在于重新提出感官中心性和总体的直接经验问题,在于批评基于一种感觉优越于另一种的‘霸权’的观点。”[15]因此,以周志强为代表的学者们选择“声音研究/声音政治批评”而非听觉文化研究的命名。这一命名申明了针对声音的关切,并非罢黜既有的视觉霸权重排座次,给听觉恢复甚至提升重要性;更拓宽了声音研究的当代性与紧迫性,即在一个日渐由倾听主导的文化消费语境中,寻找沉默和喑哑,为那些不和谐的声响安装理论的扩音器。
其次,拒绝声音之在场与主体存在的直接关联,在德里达的语音中心主义批判之后,再度寻找破解主体形而上学的新理论道路。在一个市场、技术、意识形态合围形成周志强所敏锐感受到的新“听觉中心主义”的时候,对声音的狙击就是要干扰声音与主体存在迷思的建构关系,警惕主体感官与主体存在的自然化链接。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就是用“以目听之”、用作为形象的声音阻止主体与确定声音进行对齐。这显然迥异于当下主流的听觉转向对耳朵的刻意高估,却更切合今日各类视听文化真正的接收语境。我们收看“声临其境”这样的娱乐节目,欣赏“中国好声音”的嗓音魅力,甚或驾车时听广播/听小说/听导航,听觉都不是被调用的单一主体感官,与其说这是一种新的听觉文化,倒不如说是朗西埃所命名的一种重新分配感官的资本主义新审美政治。在资本、科技、意识形态重新安置耳朵的进程中,在技术武装的沉浸式倾听激发和创造一种主体内在性幻觉的时候,声音研究正是要打破这一主体/客体、内在/外在的新二元对立。
正是迥异的学术立场,对声音研究的不同期待,导致了近乎令人吃惊的相反结论。以齐泽克为例,齐泽克和中国叙事学者傅修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卡尔维诺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作品《国王在听》(A King Listens),更有趣的是两人都援引了米歇尔·希翁的声音理论作为阐释支撑,也都将文字表征语音的跨媒介书写提升到了理论高度,但两位学者对这一小说文本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傅修延主张卡尔维诺通过对层层声音的递进描述,最终揭示出“语音独一无二的魅力”[16];齐泽克则将引诱国王的“直接生命享乐的纯粹女性声音”视为幻象,“虽然不是卡尔维诺本人的幻象——而是打破表征的封闭循环和重新加入纯粹外部的幻象,这个幻象无需阐释,仅将身体交给声音享受自身的实践”。[17]在齐泽克看来,引诱国王走出王廷的女性声音并非如傅修延所说的独一无二、充满魅力、自外部而来;这一外在的、特殊的、阴性的声音恰是主体自己的幻象,一旦被逮捕,“经过警方的彻底审讯,这名女子完全会唱一支不同的歌”。也只有现代权力主体国王而非传统君主,才会关心外在于权力主体的客体世界的声音阴谋,从仆人们的脚步声、窃窃私语到宫殿外城市上空的喧闹声,直至把皇宫变成一只巨大的耳朵。就此《国王在听》不是一部用沉默的文字写成的歌颂声音魅力的小说,而是拆解声音作为幻象的解构主义文本,它撕裂了现代权力结构仰赖的阐释循环,打破主体内在/外在的区分幻觉,即一切外部威胁早已是主体内在的分裂构成。②齐泽克沿着德里达批判语音中心主义的道路,选择彻底颠覆看与听的区分,甚至在一种有意识的倒错逻辑中,拆解正在说话的我与我的存在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敦对周志强“声音决定论”的指责,是有道理的。在有关“声音拜物教”和“听觉中心主义”的论述中,周志强几乎不对另类商榷和接受的可能报以任何期待,他太快就得出了伦理退化的“坏声音”的结论,也太急表露了对聆听者不加抵抗的失望之情。与之相反,王敦充分预留了文化差异和接收语境的空隙,对听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与了尊重。但是他并未指出的是,聆听主体的商榷与解码空间,不同于观看主体的协商与抵抗,正是声音独特的自然属性,其多意性、不确定性与幽灵性,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让子弹飞一会”而非精准狙击的开阔战场。这正是拒绝盲目搬演听觉文化研究的原因所在,尤其体现在下述对声音的物质性、身体性等“本体论转向”的探索中。
最后,拒绝盲目复制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等“后”(post-)学理论范式,寻找突破“语言转向”的新理论道路。追问声音的物质性,它的质感和时空经验,将一种唯物主义的身体参与重新写入声音研究,使得眼下兴起的声音研究正在成为突破后学范式的新理论试验场。
再以齐泽克为例,借用米歇尔·希翁有关“无声源化(acousmatization)”的研究成果[18],即主体听到声音,却无法看到声源的这一情境,恰恰意味着相较于视觉,声音始终存在着某种幽灵的自主性,永远不可能完全属于我们看到的某一具身体/主体。声音的这一准超验性、幽灵性恰恰意味着其某种“活死人”的存在,即声音没有对象,它向主体说话却不附加到任何特定的持有人身上。正在说话的我,听到我正在说话的我,并非来自一个确定的主体肉身这一见解,以声音的不可见性为声音与特定主体的链接,留出了一丝可供商榷的裂隙。正是基于这一立场,齐泽克所理解的《国王在听》中的那一纯洁的、美丽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女性歌声,不是傅修延解读的某一个魅力女性的声音,而是权力主体的内在幻象,从声音的物理属性出发,重新考察声音的情感力量和认知动能,尤其是声音在思维和身体之间扮演的继承和中继作用,都成为兴起的声音研究突破“语言学转向”的新理论方向。齐泽克论述的声音不同于视觉的幽灵特性,考克斯坚持声音研究超越语言学转向的表征框架,号召唯物主义而非形式主义的声音艺术分析,这些研究都旨在识别乃至激活声音的本体论的激进意义,都显示着对后学范式的修正与超越。
当我在MacBook上用智能语音助手,口述完成这篇论文的初稿的时候,资本市场还在不断拓展和升级各类听觉产品,还在汲汲以求独一无二的声音和声音背后的主体。声音研究正逢其时,理当以全新的问题意识,努力敲击后工业社会的耳朵,谱写全新的声音解放故事。
注释:
① 参见如下论文:王敦,“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张力与互补——与周志强商榷,探索与争鸣,2018(7);王敦,“声音”和“听觉”孰为重——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建构,学术研究,2015(12)。周志强,“听觉文化”与文化研究的陷阱——与王敦商榷,探索与争鸣,2018(7);周志强,声音与“听觉中心主义”——三种声音景观的文化政治,文艺研究,2017(11);周志强,唯美主义的耳朵——“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与声音的政治,文艺研究,2013(6);周志强,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力到中国好声音,中国图书评论,2012(12)。
② 在我看来,两种理论解读并无高下分别,需要明确的恰是王敦所说的“当我们在说听觉时我们在说什么?”傅修延旨在通过声音视角的介入,补充完善叙事理论的发展,齐泽克则锐意打破主体内在/外在的二元对立区分。
参考文献:
[1]曾军.转向听觉文化(《文化研究》第32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05.
[2]Yulia Malenkaya , Aliona Andreyeva.Fashion and Audio Branding: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Luxury Fashion Marketing Concepts.Journal of Global Fashion Marketing, 2016,7(4).
[3]乔纳森·克拉里, 许多、沈清译.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1.
[4]Murray Schafer.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Rochester.Vermont: Destiny Books,1994: 145.
[5]乔纳森·克拉里, 蔡佩君译.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5.
[6]Matthew Mullane.The Aesthetic Ear: Sound Art, Jacques Ranciere and the Politics of Listening. Journal of Aesthetics&Culture,2010,2(1).
[7] 周志强.声音与“听觉中心主义”——三种声音景观的文化政治.文艺研究,2017(11).
[8][14][15] Will Schrimshaw. Exit Immersion ,Sound Studie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Sound Studies, 2015,1(1):155-170.
[9]乔纳森·克拉里,沈语冰、贺玉高译.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
[10][11][12]Slavoj iek.“‘I Hear You with My Eyes’;or, The Invisible Master”, in Gaze and Voice as Love Objects.Renata Salecl & Slavoj iek (ed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103、104、103.
[13] Brian Kane. Sound Studies Without Auditory culture: A Critique of the Ontological Turn.Sound Studie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Sound Studies, 2015,1(1).
[16]傅修延.“你”听到了什么——《国王在听》的听觉书写与“语音独一性”的启示.天津社会科学,2017(4).
[17] Slavoj iek. 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Verso, 2012:1536-1537.
[18] 米歇尔·希翁,黄英侠译.视听:幻觉的构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