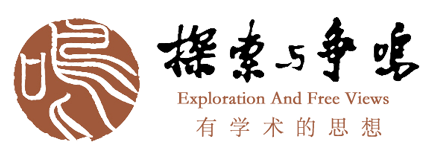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突破3亿,占全国人口的22%”。当“深度老龄化社会”不再遥远,以“健康”为核心的银发社会的高质量生活将构成“十五五”时期重要议题,其不仅关乎个体生活品质和家庭生活幸福,更攸关社会结构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发展,银发经济与健康产业迸发新机;与此同时,慢性病累积、流行病高发叠加医养实践中一些制度性顽疾,也使得“银发社会与健康中国”议题更显紧迫。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联合举办圆桌会议,着力探讨如何借力科技创新、汲取国际经验、更新观念理路、完善指标体系、健全制度保障,形成基于全生命周期主动健康治理的“中国方案”,以“银发社会治理共同体”合力推进银发社会的健康现代化进程。
彭希哲教授提出,要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个体衰老进程进行多尺度测量,形成对人口族群特质敏感的“中国人衰老图谱”,构建“身—家—群—国”的中国式健康养老模式,为全球健康老龄社会贡献基于全生命周期主动健康治理的“中国方案”。翟绍果教授强调,积极健康老龄化要把握“健康红利”机遇,构建“银发社会治理共同体”——立足于银发健康共同体的健康保障体系、依托银发数字共同体的健康管理体系、面向全龄共治共同体的老年健康参与体系。李璐研究员指出,当前银发经济发展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供给不优和政策支持不系统等问题,针对“十五五”时期新形势,应从需求侧、供给侧和政策端共同发力,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阳义南教授针对现有银发经济测度指标存在的统计范围不准、产业边界不清等问题,构建了涵盖“总指数—五大核心维度—多级细分指标”的银发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指出其实践要旨。陈友华教授指出,AI技术赋能养老健康服务的场景拓展和效率提升,但在应用中也面临技术让渡、范式异化、算法让渡、数字裂痕等困境,需要从技术改进、制度创新、社会支撑、文化调适等方面采取协同优化路径。郭未教授提出,将艺术疗愈纳入老龄健康研究与政策体系,有望重塑健康资源与文化心理支持系统在地域与阶层之间的分配逻辑,推动老龄社会的健康公平与社会融合,进而构建“有质量、无贫困、能参与”的包容性健康老龄化社会。张奎力教授强调,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均衡影响老龄人口健康,为使农村老龄人口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医”,应建立具有韧性的医疗管理制度、构建长期稳定和谐的医患关系、重塑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并引入互联网医疗等新型服务方式。杨锃教授通过对比神户模式与上海实践,指出老龄认知友好社会建设须以消解“健全者”与“残障者”二元对立的普同理念为价值基石,通过立法保障、社保兜底、社会支持、技术普惠构建健康治理体系,进而迈向全龄友好型社会。
分层是剖析作为治理客体核心的老年群体异质性的重要方法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亟需在自然分层与社会分层的双重维度和“时间—空间—制度”三维机制下,构建以精准把握治理客体特征为基础的精准治理范式。自然分层维度下,年龄分层与队列推移将推动我国老龄社会治理重心转变,老龄化的女性化与老龄性别分层间存在突出矛盾;社会分层维度下,双重优势与劣势累积机制、结果性与机会性资源匹配的梯度差异和作为新的老龄分层表现形式的数字分层,应成为老龄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关切。推动老龄社会精准治理体系优化,需要从根本上破除治理的年龄本位主义,加快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进程,关注全生命周期的多维公平促进。
谈论当代中国社会家庭危机,就必然涉及道德价值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从道德价值的绝对性出发,人们会坚持认为婚姻、家庭因其基于“上帝”或“天命”而神圣化、永恒化;从道德价值的相对性出发,人们则会主张婚姻、家庭因立足“个体”而世俗化、时代化、多样化。故基于家庭观上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去考察社会,该社会是谈不上所谓的“家庭危机”的,“家庭危机”只是一个“伪问题”。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全球化中资本逻辑驱动下对个人利益追求的日益最大化、极致化,一旦我们从绝对与相对这一思辨理论回到现实,就会发现这种“家庭危机”的确发生了,并且它也成了“真问题”。而解决这一“家庭危机”的唯一途径并非仅仅回归传统家庭,而是使自己置身于经过现代化洗礼的既强调“个体本位”又强调“亲亲为大”的“双重本体”之中。
针对当代西方政治学家对儒家政治哲学的三点主要质疑,作为当代儒学重要流派的“生活儒学”的政治哲学申明三点要义:一是构建作为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生活儒学”思想体系,以此为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奠定基础;二是构建生活儒学的次级理论——“中国正义论”,即情感伦理学的儒家表述“仁爱正义论”,以期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形态——“国族自由主义”;三是揭示儒家的自由传统,进而阐明儒家的“自由保守主义”本质。
《民法典》适用方法论中的“超越文本主义”并非是对“文本主义”的否定,而是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推动中国民法向回应型、开放型法转变的有益尝试。“超越文本主义”强调在法律适用时应兼顾立法者意图,融贯性地解释与遵循法律原则;此种主张契合我国《民法典》编撰中体现的创新性特点,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绿色原则等开放性条款融入法律适用提供通道。然而,“超越文本主义”亦可能带来削弱法律安定性的担忧,包括弱化法律文本的权威性、冲击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以及使法律适用实践的操作性复杂化。为此,必须要在“文本主义”与“超越文本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在明确文本主义的优先地位的前提下,廓清“超越文本主义”的适用边界,包括立法意图解释的边界、原则或价值融贯解释的边界以及功能解释与动态解释的边界。此外,应通过对中国司法实践案例的总结,提炼出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裁判规则和解释方法。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完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治建设的主线,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需要国家干预”形塑了“市场需要—国家干预”的理论逻辑,既为国家对市场实施干预行为进行了合理化证成,亦在理论上明确了国家干预行为之界限,纠正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当前,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趋势下,市场既有“健康”的需要,亦有“发展”的需要;相应地,政府既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亦要促进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国家干预”在干预需要的判断、干预手段的发展以及干预绩效的评估上需要进行创新。为此,在干预需要的精确判断上,数据、算法应成为判断市场是否有干预需要、政府何时提供干预的基础;同时政府应审慎利用干预权力,避免权力的过度扩张。在干预手段的创新上,“促进发展”应当扩充进国家干预的内涵之中,同时关注干预手段的创新及不同干预方式的组合。在干预绩效的准确评估上,结合数据、算法分析、人工智能等新兴要素与技术,赋能“需要国家干预”对干预绩效的评估,促成“国家干预循环”。
乡政与村治的合流及冲突并存是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主要关系形态,由此产生的假想科层关系既不能单纯归因于乡政的介入,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村治的“草根”想象,其是乡政与村治合谋的结果,集中表现为党政分工的制度逻辑、权力运行的治理逻辑、资源追逐的分配逻辑、动员策略的话语逻辑等。经由假想科层关系导致的“法治悖论”本质上是乡政与村治合意产生的副产品,破解思路不能就法治而论法治,而应该回到避免合谋的假想科层关系这一前提。法治化是乡村基层治理的必然道路,并不能因为所谓的“法治悖论”而缓进或摒弃,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乡村基层未来秩序建构的形态、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关系向度、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制度空间,推动从传统的乡政村治到乡村基层治理的转型,形塑新时代乡村基层治理新秩序。
当前数字治理实践中存在着量化与简化、整体与自主、集成与透明、标准与精细、效率与感受等多重悖论。这些悖论根植于工具理性崇拜与制度路径依赖的交互作用,由此导致数字治理实践往往偏离预期目标,甚至产生逆向效应。数字技术虽未达到预期效果,却在公共话语中被建构为“治理神器”,产生了“现实与叙事”之间更深层的悖论。因此,数字治理的未来转型应当认清技术边界、革新治理理念、注重社会感受,实现有技术边界感、制度突破性和体验真实性的数字治理范式,避免陷入炫技治理、数字空转和数治神话的误区。
在DeepSeek热潮的影响下,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被大范围应用于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如何在社会治理中确保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可信日益重要而紧迫。社会治理视角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可信,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能力与社会治理问题的能力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可以建构社会治理中的可信人工智能大模型框架。这一框架包含五个维度:一是深入理解模型运作原理,二是明确模型在任务上的预期表现,三是预判模型可能产生的衍生影响并进行主动验证,四是建立模型之外的第二套备用方案,五是利用大模型治理数据促进模型优化迭代。社会治理中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治理如同长江的水患治理一样,需要超越“根治”观念,确立“韧性治理”模式。
士,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从“士”字的古字及其释义,透出“士何以产生”的远古根源。从起源讲,原始之士拥有知识的整体性。从原始时代的士-王一体,到早期文明中王、诸侯、大夫、士的展开,这种知识的整体性一直存在。士在春秋战国的理性时代产生,促成其知识结构的进一步提升。新产生的士,在知识的新建构中形成以道之宇宙、仁之人性、法之政治、侠之社会为基点并互为补充的知识整体结构,并展开为多种多样的面向。士的特质又集中呈现为师-吏-文的统一,师与道统相连,吏由政统产生,文与审美相关。师-吏-文一体的士,在从秦汉到元明清的演进中,有着复杂的类型展开和丰富的美学呈现。从士的起源、形成、演进的特点来看中国美学的特色,或可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深入展开的一条新路。
历史书写中道德与情感的关联是一项核心议题。情感史在近年兴起之后引起了较多重视,而战后日本民众史的兴起为此提供了典型案例。传统史学注重道德训诲,而兰克学派主张的客观叙事在二战后受到挑战。日本民众史学者色川大吉、安丸良夫和鹿野政直等人通过发掘底层民众的经历,揭示了愤怒、同情等情感与正义感等道德的交互作用。这一研究不仅改造了明治日本所开始的近代史学传统,还通过“通俗道德”等概念,展现了历史叙事的复杂性与社会价值观的深层联系。
自20世纪80年代彼得·斯特恩斯(PeterN.Stearns)提出“情感学”研究以来,情感史的理论方法不断更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实证研究不断深入。历史学家对情感的记录并非始于20世纪。早在古代史家的著述中,我们便可发现时人的各种情感。情感贯穿于古代史家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和军政外交的叙述中。这并非因为古人的情感更加充沛,而是因为情感本就是人类固有的特质。古代史家对人们言谈举止和历史进程中情感的记录表明,情感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源远流长。但近代以来,随着历史学科学化的推进,情感与兰克史学“客观治史”的追求越来越难以兼容,以至遭到冷落。情感史的兴起与近现代史学的发展演进息息相关。它的兴盛不仅冲击了近现代史学传统对它的贬斥,也反映出当代史学的发展方向。